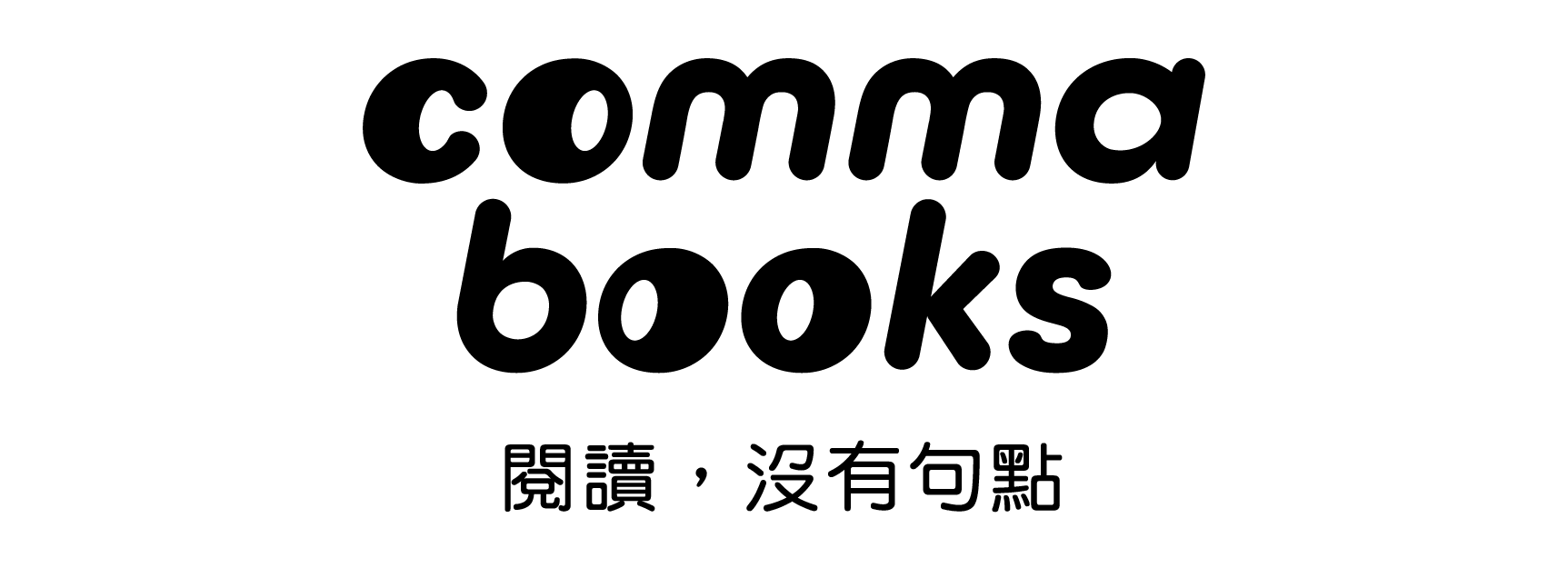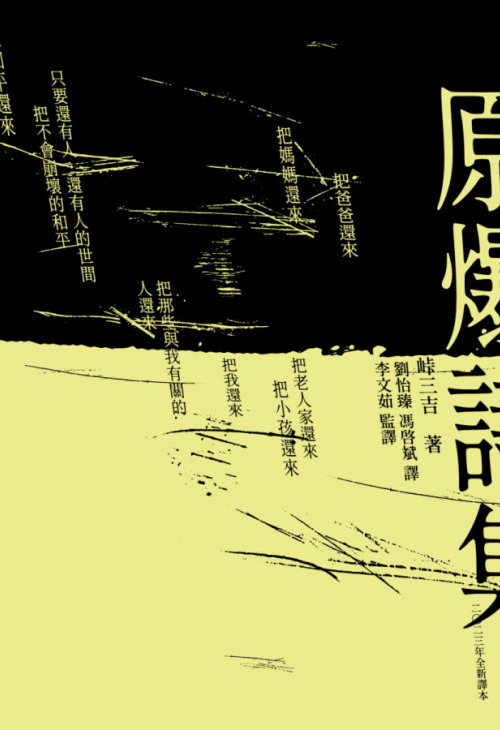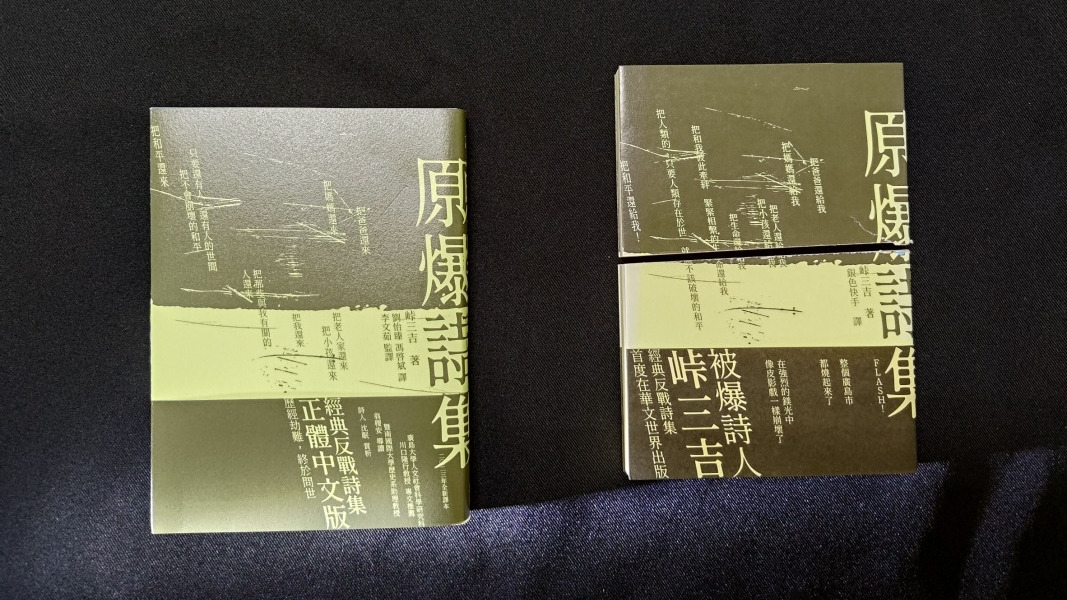
如何表現卻不濫情——煮雪的人評《原爆詩集》
2011年初訪廣島,我在平和紀念公園看見一塊峠三吉詩碑,上面刻的是《原爆詩集》的序詩:「把爸爸還來 把媽媽還來/把老人家還來/把小孩還來/把我還來 把那些與我有關的/人還來/只要還有人 還有人的世間/把不會崩壞的和平/把和平還來」。原文僅用平假名寫成,且沒有複雜的文法,容易聯想到這可能是一名兒童的控訴,增加了整首詩的力道。翻譯過後儘管只能犧牲全平假名的效果,一連串簡單明瞭的命令句,依然能讓這些詩句深植異國讀者的心——表面上的零技巧,就是峠三吉在此的技巧。
《原爆詩集》的書末賞析中,詩人沈眠提起了「文學能否再現苦難」這個爭論不休的命題。其實廣島的作家們也曾為了是否該繼續書寫原爆,分別於1952年、1960年與1970年代末進行過三次的原爆文學論爭。
那些試圖描寫苦難的作品若是遭遇批判,多半被說不夠真實,或者太過濫情。濫情確實是寫作者該忌諱的,然而「不夠真實」該是針對文學作品的批判嗎?或者說,文學作品是否該追求真實?
真實可能是毫無情感的,桑塔格曾在《論攝影》中寫道:相較於紀錄片中的手術過程令人畏縮,親眼目睹手術反而毫無不適;真實也可能是暴力的,基於求真而促成的悲劇並不亞於謊言,以真實之名發動的迫害也絡繹不絕。人類的和平與溫情,也許從來就不是建立在全然的真實之上。這並非說我們不該求真,而是不要輕易為真實代言。
這本詩集在台出版之際,社群媒體的書訊中引用了上述的序詩,果不其然有人去脈絡地在下方留言針對日本的仇恨字眼。若是有閱讀這本詩集,甚至只要讀過公開於網路上的書序,就能夠知道作者關懷的對象不只是廣島的人民,而是全人類,大聲疾呼的對象是「可能使用核武的任何角落」。這些人卻因從小被灌輸的仇恨,或是心中輕易斷定的真相,而選擇忽略原爆被爆者與受難者遺族至今如何批判軍國主義,如何批判近年來逐漸右傾的日本政府——這何嘗不是二元論輕易為真實代言的後果。
峠三吉在《原爆詩集》中示範了良好的平衡:儘管他無疑經歷過廣島原爆現場,多數詩作採用的卻是旁觀視角,例如〈火焰〉:「被拉往屠宰場的牛群/摔落河岸/一隻灰色的鴿子/蜷縮著翅膀跌落橋上。/一個 一個地/從煙灰底下爬出來後/被火吞噬的是/四隻腳的/無數的人類。」而〈年邁的母親〉、〈墓碑〉、〈總有一天〉、曾被選進日本教科書的〈臨時包紮所〉等作,則是以母親、學生、少女等他人的視角書寫。這些作品顯然並非詩人的親身經歷,想像力的介入卻也無礙文字所呈現的震撼,也減少了濫情的可能。
詩,作為最常被完整傳遞的文學體裁(我們可以簡述一部小說,卻難以簡述一首詩),比起再現真實,更重要的是如何表現,以及如何表現卻不濫情——關於這點,《原爆詩集》可被視為模範之一。
(本文經原作者「煮雪的人」授權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