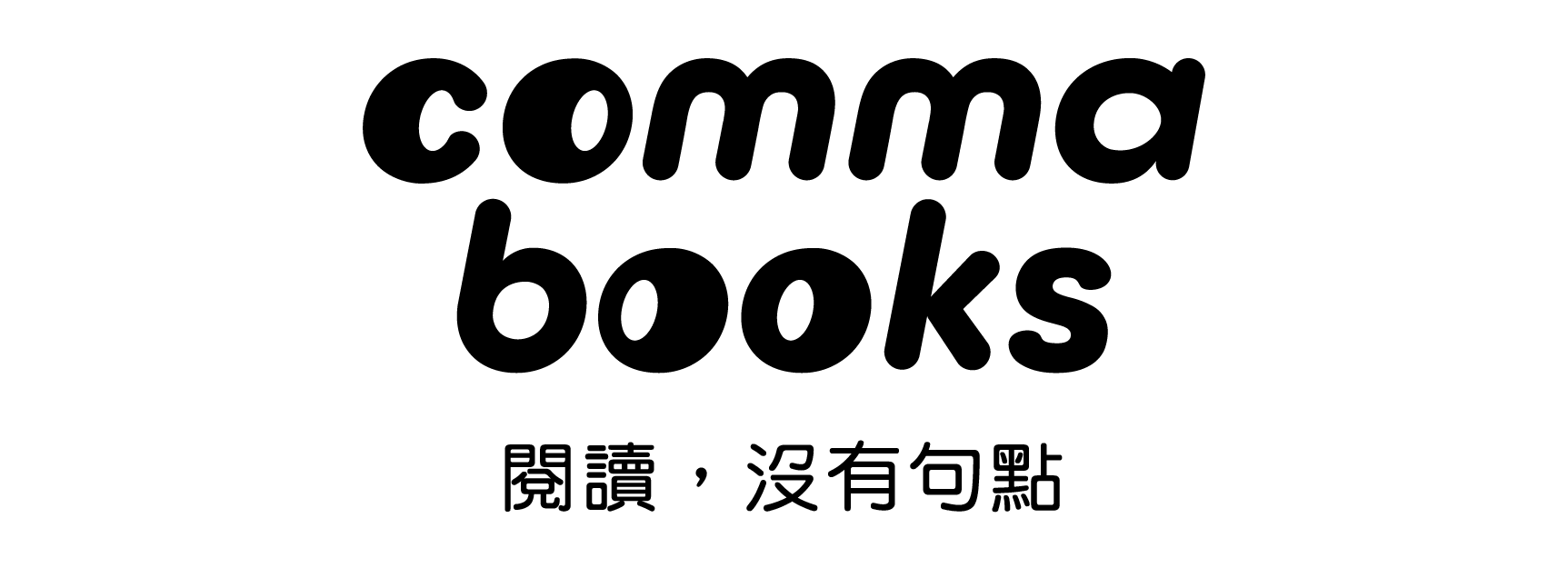作者:廖祿存/攝影:達瑞
2024/12/31
生活改變我們的詩——鄭聿、林禹瑄、曹馭博三方對談
逢旅歐多年的林禹瑄返台,跨出版社籌辦了一場分享會,讓平日各在一方的三位創作者聚首,談談如何看待生活(居住移動、職業換置等等現實)與詩之間的連動關係。
Q:從第一本詩集至今,生活有了什麼顯著的改變?
- 林禹瑄:當年在X19的比賽中脫穎而出後,獲得了出版詩集的機會,《那些我們名之為島》出版時,還在讀牙醫系一年級,從那之後,換了兩次職業,也換了一個國家生活。
牙醫系畢業後,因為不喜歡當時的工作,又覺得要在原生地做出改變比較困難,衡量自己懦弱的個性後選擇出國。(鄭聿:選擇一張機票出國不是更需要勇氣嗎?)那時候讀了《賈樟柯電影手記》,有個想法影響了我——「留下來最需要勇氣。」所以我選擇離開,到了無法過第一志願人生的集散地——布魯塞爾(純粹是簽證的便利性成為浪遊者的第二選擇)。在比利時成為了一位獨立記者,因喜歡寫作又必須養活自己;但是對於文學還是存在著想像,儘管已經沒有過往的強烈分享欲望。
剛好在抵達生活的谷底時刻,收到二十張出版表達出版詩集的意願。 - 曹馭博:第一本詩集《我害怕屋瓦》出版後,達到人生的一些目標。雖然從大學詩社開始持續創作,一直到二○一七年得到林榮三文學獎時,才覺得自己寫的是「詩」。得文學獎、詩集出版、臺灣文學獎蓓蕾獎,一切接踵而來,讓我誤判了自己,也得罪了許多朋友……。詩集出版後,家人陸續生病,下坡狀態的家中經濟,更雪上加霜,得獎獎金都用來幫助家裡。並且,開始過著沒有詩的生活,我找了一份內容農場的編輯工作,過得很痛苦,為了錢還是撐了一陣子。有一天,爸爸突然問我有沒有繼續寫?他認為我在創作狀態裡比較帥。事實上,第一本詩集達成許多成就後,當下覺得可以去做別的事了。後來疫情來襲,加上辭職的緣故,趁機整理出《夜的大赦》。
- 鄭聿:記得首部詩集《玩具刀》的分享會很緊張,因為從一個讀者的身分轉變為作者。平時我是比較害羞,比較不願意跟人家交談的人,沒想到就此改變。以前常覺得很多詩人怎麼沒有繼續寫,是因為工作嗎?工作怎麼可能讓一個人沒辦法寫東西?直到寫第二本《玻璃》,思緒漸漸簡潔,覺得不太需要透過創作說出來。二○一七到二○二一經歷了好多社會事件,但我的創作跟社會的聯繫比較少,直到二○二二年離職,覺得應該把時間留在自己身上,創作是我擅長的事情,並且想為自己留下什麼。部分原因來自於成名的焦慮,以及自我的再定位,把創作當作生命的擋箭牌。接下來想寫跟台灣更相關的作品。
最近把《玩具刀》刪去一些詩後修改為《玩具鞘》(先發行電子書,二○二五國際書展時會有紙本書),至於為何是刪掉而不是修改?原因是以前寫得太枝節了,如果改成現在的東西,那就不是第一本詩集了。初衷到底是什麼,真的難以回想。
Q:如果生活是詩的養分,如何讓創作回應生活;生活的什麼面向會回過頭來改變你的詩?
- 曹馭博:在淡水租屋處,有個在雨傘運動期間消失的鄰居,當房東拿鑰匙打開他的房間時要探門關心的我一同整理。房間裡,他的生活痕跡那麼地清晰,腳踏車、衣服、書籍……。這給了我很大的震撼,讓我思考如何將日常中的觀察和機緣寫進詩裡。疫情後,和女友協調,一個人上班,一個人在家。淡水我認識了許多人,包含和我的家庭一樣遭受打擊的人們,在家的我,原本想寫關於金融的小說,後來調整成為經歷金融風暴的小說。在即將完成《夜的大赦》時,嘗試寫下了一篇小說,後續漸漸完成《愛是失守的煞車》。小說的細節跟詩不同,目前的我對於兩種文體都抱持著興趣。
- 林禹瑄:生活像鏡子反射在創作裡,生活中發生的事情,不管是有意或無意,總會跑進自己的生活裡。在歐洲生活時,難民和移民是進入生活的事件。至於如何看待生活,以及看待的角度,卻沒有辦法透過創作來完成,反而需要透過時間讓它自然發生。如果我看東西時,視野並沒有拉高;視角也沒有改變,就會停止重複自己的創作。當我完成第二本詩集時(《夜光拼圖》,二○一三),發現生活開始重複,於是,我停止繼續寫詩。
- 鄭聿:活跟創作,本來就綁在一起。一般而言,創作很容易定義,相對來說,你要怎麼定義生活呢?要到什麼程度或是自覺,才是「我在生活」?如果沒有好好生活的話,那跟生活綁在一起的創作,是不是就會一起消失?
Q:曾考慮停筆創作嗎?如果有是為了什麼?如果沒有,又是什麼支持著你?
- 林禹瑄:有一兩年的時間幾乎沒有寫詩,因為陷入了自我重複,停筆的時間不會令人害怕,反而擔心峰頂已經過了。如果生命明天就結束了,也不會有遺憾,覺得足夠了。高中時,學校請來瘂弦演講,他說:「這幾年變得特別胖,可能是沒有寫詩的緣故。」我也常常這樣砥礪自己,太過安逸就沒有辦法寫詩了。
- 曹馭博:看到其他人寫的詩超過自己,往往會想說那我幹嘛繼續寫,像是楊智傑出版《野狗與青空》時,就覺得最好的詩都被他寫完了,我何必再寫同一方向的詩呢?又好比蕭宇翔開始以長詩來處理科幻素材,之前讀到的總字數幾乎是我的詩集的好幾倍,那我也不必去寫長詩了。以前不會比較,只會埋著頭寫,現在想想,實在很幸福。雖然翻譯也算是創作的一環,但不寫這件事的確讓我很焦慮。
- 鄭聿:跟創作之間的關係,比較像是在一起很久但沒有分手。二○一四至二○二二,創作上遭遇困頓,但還是半年左右會再想要寫詩。可能是有我想要關心的事情吧,我在乎大家也在乎的,這也是我想創作的原因。

不同世代的三位詩人分享了生活與創作的關係,現場聆聽者有的陷入深思、有的豁然開朗,詩是永恆的季節,是詩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還是我們的生活改變了詩? 第一人稱敘事所寫下的第一時間感受,無可逃避的生活,隨時可能變形──方便摺疊收進多邊的小宇宙。他們說:要先好好進入生活,你才能夠好好寫詩。

《普通快樂》
作者: 鄭聿
出版社:二十張出版

《春天不在春天街》
作者: 林禹瑄
出版社:二十張出版

《夜的大赦》
作者: 曹馭博
出版社:雙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