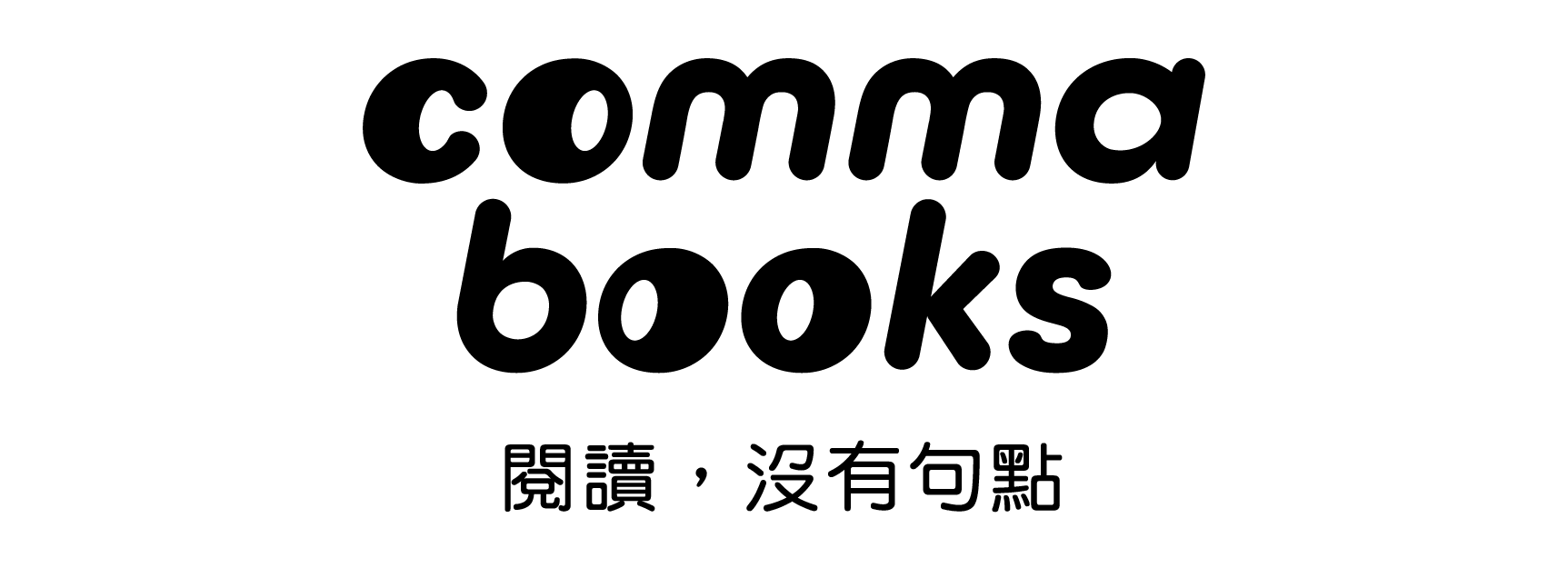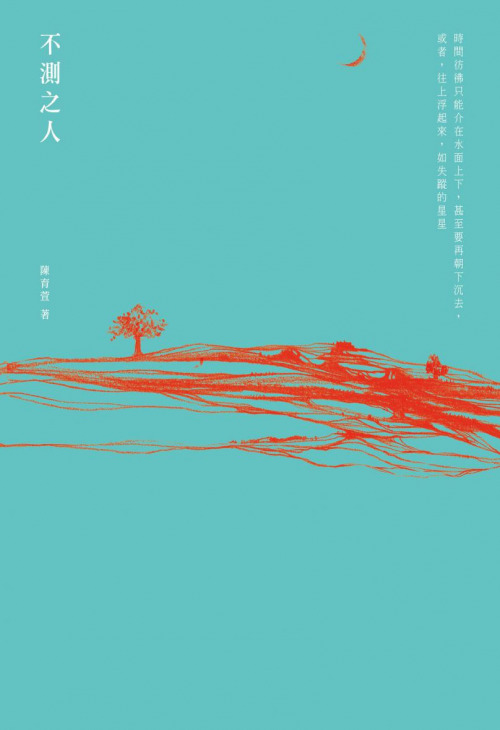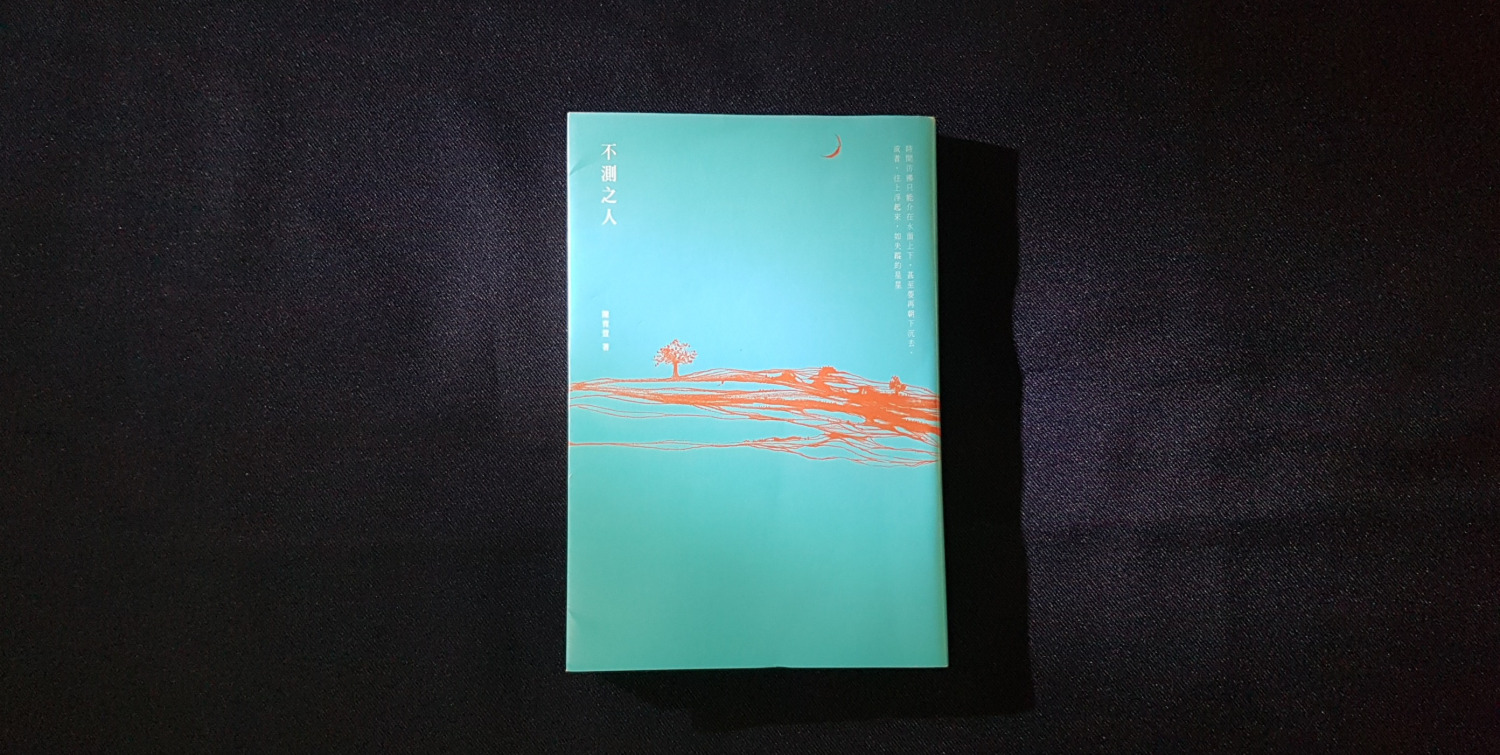
存在即延續:小說家林俊頴推薦《不測之人》
二○○六年九月,我提著簡單的行李匆匆到後山、東華大學英美系的創作研究所報到,領取一個寓意可以複雜甚至衝突的頭銜:駐校作家。
那時候,木瓜溪以南,火車鐵軌與台九線以東,在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間的那片平地,空曠,安靜,朝夕霧靄,雞鳴狗吠,白雲依著山稜線大作文章,且側門志學街還未拓寬,很有遺世獨立、潦草不文的況味。
向來只愛在自己的軌道按自己的速度運行、憚於人際往來的土象星座人如我,很快對「上課/教書」一事鬆了一口氣。育萱是早一年考上,但延遲入學,納入我接觸最多的第七屆碩士班,男女生各五位,一整班好像初夏蓓蕾飽實的荷花池,太陽下盡是新妍與光亮,一一比我在同樣年紀時對寫作有更濃厚的熱情,更強烈的意願,更專注的目標。但我壞毛病,內心始終矛盾也困惑著,將文學創作收進學院體制內,是好的嗎?是正確的嗎?寫作,這一門(最?)古老的手工藝,於今看似幾乎沒有入門門檻,實則道阻且長,從來是罕有師承,自學自悟自證的一人道路,怎麼教?我慶幸他們多保有的是遠非幼態持續的那一份純真,那麼,這一段時日就是他們且濡沫且練功的幸福歲月吧。難逢難值。
偶爾,我坐他們的機車與之一同遊蕩,聚餐,去他們難以分辨是田地是曠野中的租屋,大風吹動屋外枝葉,夜裡更覺得不知是置身哪裡的邊陲荒陬。恐怕只有我知道並暗暗為之心驚,他們的青春煙火很快要給時代的大風吹落。
一班裡,育萱最質朴木訥,口齒少鋒芒。一次偏又她自己起頭玩笑,遭幾個男生圍攻,我試圖阻擋,男生駁我,老師你不懂啦。我只好閉嘴。然而,最先得文學大獎的卻是她。
作品折射作者的個性、材質、品氣,理所當然;進一步洩露其深層如礦脈如伏流的意識、靈魂—占星術太陽、月亮座落星宮的互為補綴、辯證?於讀者,這兩者的加總,也是發現,昆德拉所謂唯有小說才能致之的發現。因此,認識進而熟悉一位作者,如同那句老話,時間是最好的審判。
作者書寫其人倫關係肇始的生長之地,我不說「鄉土」,也是理所當然。那是無從割斷的生長點,或者是「多年後」才猛然醒悟的啟蒙點。而有膽識的優秀作者拒絕將它簡化、浪漫化。
《不測之人》藉著一男性鬼魂穿越時空與記憶,是留戀也是守望他生前的親人、朋友、家鄉,哀悼傷逝的意思少,多的是一種深情款款的平視,這些人與事,這塊土地,為生計為發展為理想或者因為貪婪無知而傷勢累累,整體的惡化狀況短時間不可能有起色,那麼,他們亦即我們究竟要往那裡去?這是一個既奇詭又沉痛的視角與設計。這也是育萱給自己出的一道難題,更是再一次質問「小說」,我寫出來了,那又如何?
當下的台灣,不過三十年時間,歷經「政治是高明的騙術」的膛炸,「全民大悶鍋」、「全民開講」的退乩,神鬼退位,滿目荒涼,即便犬儒、訕笑都倦怠無力,虛假的則比真實的還更大聲更動人。《不測之人》在這個時候出現,如同它最後一章的名字〈度〉,小說中的仁仔溪、陂仔尾、關帝廟,母親、妻子、好友,讀來如同在一輛疾馳而去的載卡多後座,我們背向前程而面向他們,顛簸中不願將目光須臾離開。
昔年達摩一葦渡江,我父母及更上諸輩則用「過身」(台語)指說死亡,雖然這寄居旅世的肉身,白駒過隙,但他們不相信船過水無痕,他們相信存在即延續,鬼魂並非虛無的產物。蘇進伍這隻新鬼要喚起的是質疑,是對抗,是「寧鳴而死」的小說力量,因為小說家陳育萱是如此心繫斯土斯民,她與代言她的鬼魂知道,人鬼替換,不是清算的終結,而是辨識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