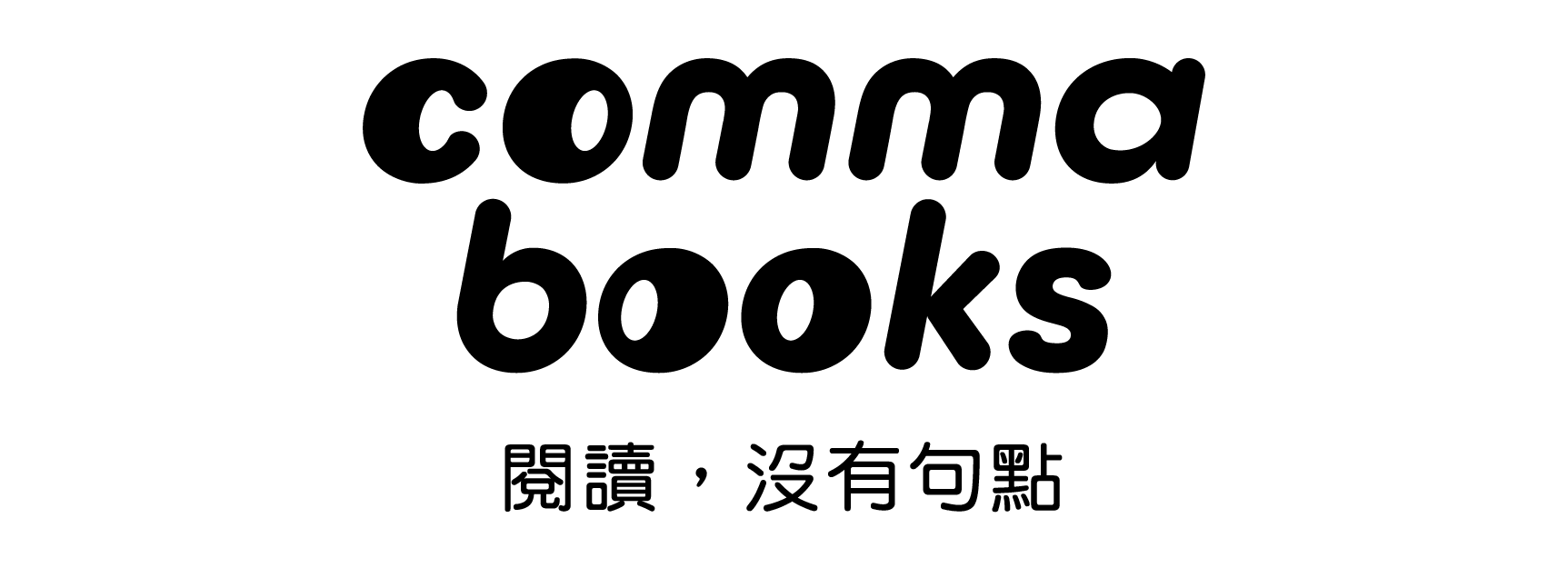永遠不退流行的大幽默家——談瑟伯《想我苦哈哈的一生》的幽默書寫
◎淡江大學英文學系 蔡振興 教授
大幽默家的養成
瑟伯(James Thurber)於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八日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日死於腦栓塞,享年六十七歲。華文讀者對瑟伯或許感到陌生,其 實他是全美知名的小說家、散文家和漫畫家。他的發跡與《紐約客》有關,他的貴人就是名作家懷特(E. B. White)。瑟伯於一九二七年二月遇見懷特,懷特隨即就把他介紹給當時的《紐約客》主編羅斯(Harold Ross),瑟伯就此與《紐約客》結下不解之緣,其作品也深獲現代主義作家海明威、艾略特(T. S. Eliot)、葩克(Dorothy Parker)等人的喜愛。
《生活》(Life)雜誌稱他是「美國最令人不安卻非常有趣的幽默作家」。早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時代》(Time)雜誌更將 瑟伯遴選為封面人物,肯定這位作家在文學上的成就。二零一三年,由班史提勒自導自演的好萊塢電影《白日夢冒險王》,就是改編自瑟伯一九三九年的同名小說, 這也說明了瑟伯的作品與我們十分接近,提供了質量俱佳的幽默閱讀體驗。
瑟伯的母親瑪麗(Mary Fisher)是一位天生的喜劇演員。父親查爾斯(Charles L. Thurber)在一八八四年認識了瑪莉,那年他十七歲,經過八年書信往來和約會,查爾斯終於抱得美人歸,於一八九二年在距離女方家不遠處的一座教堂舉辦 婚禮。婚後,兩人育有三兄弟:老大威廉(William)、老二詹姆斯(James)、老三羅伯特(Robert)。
很不幸的是,一九零一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天下午,哥哥威廉在玩射頻果遊戲時,不小心將六歲的小詹姆斯左眼射瞎。這個遊戲 被批評家比喻為「威廉泰爾的考驗」(The Trial of William Tell)。據說泰爾是一個獵人,由於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Austria)的暴君葛斯勒(Gessler)在中央廣場立了一根柱子,上面掛著皇家帽子,規定居民經過時必須向帽子敬禮,違者將受到處罰。有一天,泰 爾經過廣場時,因未向帽子敬禮而被捕。為了處罰泰爾,葛斯勒要泰爾射中放在自己兒子頭上的蘋果,才願意釋放他們。
泰爾成功地射中蘋果,但哥哥威廉自製的箭頭沒能射中蘋果,反而射傷詹姆斯的左眼。右眼後來也因交感性眼炎 (sympathetic ophthalmia),「一種合併肉芽腫的葡萄膜炎,使得一隻眼睛因為手術或者意外而創傷之後,造成對側眼睛也出現發炎的情況」,從此詹姆斯的右眼便蒙 上「一層陰影」,一九四五年以後,瑟伯的視力變差,幾近全盲。這對他的工作和創作,帶來極大的不便。
噢,幽默、幽默、幽默!
文學上,瑟伯被喻為「幽默大師」。其實,「幽默」一詞是英文 humor的譯音,這個字的原始意義來自古希臘。根據古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描述,人的脾氣和個性與身體的四種體液 (humors)有關,包括血(blood)、粘液(phlegm)、黃膽汁(yellow bile)和黑膽汁(black bile)。人的樂觀、冷淡、暴躁、憂鬱等四種個性就是這四種體液的表徵。儘管希波克拉底努力區分醫藥與迷信,他仍相信這四種體液若是分泌不平衡,將會導 致身體疾病的發生。到了中世紀,人的內在個性與外在自然中的土(earth)、空氣(air)、火(fire)和水(water)相互呼應,因為人性 (human nature)和大自然(Nature)中的熱(hot)、寒(cold)、濕(moist)、乾(dry)是相通的。例如,有黃疸的人屬於燥熱(hot and dry);憂鬱的人是黑膽太多,屬於燥冷(dry and cold)。著名的丹麥王子哈姆雷特(Hamlet)的「古怪脾氣」(antic disposition)則是「憂鬱」的徵候。因此,今天我們常講的幽默感(sense of humor)其實主要是針對這些不同個性的深描所產生出來的喜感。
幽默感是一種「情動力」(affect)的表現。表面上,幽默感似乎只為搏君一笑。然而,幽默感有其內在邏輯:透過某 種看似「不連續」的類/對比去傳達更深刻的文學內涵。瑟伯的幽默感異於十九和二十世紀的美國作家,如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李伯大夢》(Rip Van Winkle)或馬克吐溫的《哈克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後兩者對大時代的不同社會階級差異有所批判,然而,誠如布雷克(Stephen A. Black)所言,瑟伯對過去和現在的階級差異或尋找美國夢的描寫不感興趣;他非但對過去不會生氣,也不對未來感到憂心忡忡。再者,瑟伯筆下的小說人物絕 非代表著大時代的英雄,或具有救國淑世抱負的理想人物,而是一般普通的老百姓。別的小說家或許偏好描述成功的個人,或對處於動亂中的大時代故事特別有興 趣,但在《想我苦哈哈的一生》一書中,瑟伯所要帶給讀者的,並不是引領讀者瞭解《時代》雜誌中的世界大事。誠如作者在序中所言,他所要傳達的只不過是「作 家的人生遭逢」而已。
儘管作品中的背景約略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對國際局勢或戰爭僅止於輕描淡寫,並未對大時代為小人物所帶來的種種苦 難作出尖銳的批判。在〈我在徵兵委員會的夜晚〉,敘述者說他因視力問題而無法從軍。文末,他寫道:「有個早晨稍晚的時候,沒多久前才做完最後一次體檢的我 被又是鐘聲、又是汽笛聲的噪音給吵醒。那噪音越來越強、持續得越來越久,也越來越亂。停戰了。」這一句話說明第一次世界大戰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早上 十一點整結束,而「停戰了」這一句話也為這個故事畫下完美的結局。
瑟伯的幽默寫作分析
小說的場景是美國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主要人物乃是敘述者一家人,包括爺爺、姑姑、父親、母親、傭人和敘述者等人的生 命書寫。小說中,敘述者有三兄弟:老大荷曼、敘述者詹姆斯、老三洛伊,但這三兄弟的名字不是作者家裡的三兄弟(威廉、詹姆斯和羅伯特)。即便如此,瑟伯 《想我苦哈哈的一生》一書還是充滿濃濃的自傳色彩。在創作時,瑟伯認為他的幽默感主要有四種類別:一、潛意識的神經質;二、難以收拾的偶發事件;三、一連 串的錯誤事件;四、刻意安排的效/笑果。因此,我們可以透過這四種視角來分析瑟伯的幽默書寫:
- 潛意識的神經質
〈床塌之夜〉描繪敘述者一家人因為父親突然想在閣樓睡覺,再加上敘述者的表哥貝爾剛好來家裡作客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 根據作者的綜述,這個家的成員頗具「特異性」(singularity): 貝爾深怕睡覺時會忽然斷氣,所以每隔一個小時都會醒來一次以確定自己還活著;敘述者的阿姨梅莉莎害怕會死在南大街上;舅媽則每天晚上害怕會有小偷進來,因 此每天晚上都把值錢的東西準備妥適,好讓小偷自行取用。人物安排妥當,接著便透過一連串「誤認」(misrecognition)和「誤解」 (miscommunication),讓小說中所有睡覺的人都被吵醒,並展開一段荒謬爆笑的情節。
在〈不推不動的車〉中,敘述者回憶二十五年前一部車齡二十年的老爺車被電車撞壞的故事。有趣的是,作者運用「自由聯想」的離題技巧,把不相關的角色用「風險」和「危險」的主題串連在一起。故事中老爺車隨時有熄火的風險;而敘述者的母親杞人憂天,害怕家裡的留聲機可能有 爆炸的危險,她也同時害怕漏電的危險,「電在無形之中,正一點一點滴進屋子的每一個角落。只要牆上的開關沒關,她就認定電會從沒插插頭的插座裡漏出來」。 這個故事讓讀者對敘述者的母親的個性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整體而言,她無法區別風險(可以事先評估災害或傷害)和危險(臨即性且不可逆的災難或傷亡)。這種 認知上的差距能讓讀者不自主地莞爾一笑。
- 難以收拾的偶發事件
〈大壩潰堤了〉是無中生有的「末世論」(apocalypse)最佳寫照。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三日,鎮上有人謠傳俄亥俄 州的賽奧托河(the Scioto)的大壩潰堤了,約有兩千名市民因此紛紛加入一場歇斯底里的逃難潮。敘述者的爺爺再次誤以為這些人因為打仗敗北而撤退,不想當逃兵的他不肯配 合逃離,家人只好用燙衣板把爺爺打昏,然後加入市民的逃難潮。事實上,這場歷史上的大逃難源於一場誤會,只聽到有人說:「大壩潰提了,往東走!往東走!」 儘管當時的民兵拿著擴大器對逃難的群眾大聲疾呼:「大壩沒潰提!」但是驚慌的群眾不但不相信,內心反而更加恐懼。這場千人大撤退在倒數第二段真相大白後, 嘎然而止,最後一段雲淡風輕的描寫,反而呈現出巨大的反差與傳奇色彩,同時幽了內文中外表長的有點像英國詩人布朗寧(Robert Browning)的名醫梅樂里一默,是很高明的回馬槍。
〈鬧鬼夜〉發生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凌晨一點十五分左右。當敘述者沐浴後,忽然聽到有男人繞著樓下的餐桌快步行 走,懷疑「家裡有鬼」,後來兄弟倆又聽到腳步聲,於是哥哥衝回房間,敘述者則「猛然甩上樓梯口的門,還用膝蓋頂住門面」。老媽先是聽到甩門聲而感到納悶, 隨後又聽到腳步聲,於是二話不說,立馬拉開臥室的窗戶,俯身拾起一只鞋子逕往鄰居臥室窗戶一扔,打破鄰居玻璃,在鄰居報警後,騷亂依舊未息:敘事者的爺爺 剛好醒來,以為現在正值是南北戰爭期間,不但把警察誤是米德將軍的逃兵,甚至開槍誤傷了警察。
〈夜半又驚魂〉則是羅伊和詹姆斯兩兄弟晚上因睡不著而去吵老爸的故事。有一天羅伊因輕微發燒而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到了 凌晨三點左右,因為睡不著,羅伊就跑去老爸的房間搖他、嚇他,並說:「巴克,你的大限已至!」半年後,敘述者也因想不出幾個紐澤西的城鎮而睡不著,於是像 弟弟一樣,也在凌晨三點左右去鬧老爸。在瑟伯巧手安排下,單純的惡作劇一路演變成全武行,父子最後大打出手。幸虧母親出來勸架,才結束這場鬧劇。
- 刻意安排的效/笑果
敘述者在〈傭人小記〉回憶家裡曾聘請一百六十二位幫傭,並將其中較有印象的幫傭做有趣的介紹。在瑟伯刻意安排之下,每 一位傭人不僅個性十足,也有不同的瘋狂小事:生性害羞的朵拉,會在晚上朝房間裡的男人開槍;臉色紅潤的葛緹是個酒鬼,半夜喝茫了吵醒大家就說自己在幫主人 撣灰塵;歡艾瑪(這名字本身也是刻意安排的笑點)容易被催眠;長相標緻的華西蒂,總有辦法找回敘述者母親的失物;彗星般來到敘述者的家,又像彗星般離開的 杜迪太太;說起話來咬字不清,有著濃重黑人口音的羅伯森太太,茲因一件小事情—即暖爐後方傳出怪聲到底是蟋蟀(cricket)還是報死蟲(uh death watch)—而與敘述者的父親嘔氣,最後辭職;默默工作的艾妲,效率極佳,但壓抑太久竟然暴走了⋯⋯。
〈愛咬人的狗〉是毛小孩瑪格斯的故事,令人想到一樣由班史提勒主演的誇張喜劇《哈啦瑪莉》(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中,他與一隻看似無害可愛實則兇猛無比的小小狗所上演的激烈對決場景。瑪格斯喜歡咬人,害敘述者的母親每逢過年,都要送禮物給被咬過的鄰居。瑪 格斯什麼都咬,就是不敢咬敘述者的母親和老鼠。瑪格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雷電交加的暴風雨,正是所謂的「惡狗無膽」。正因瑪格斯會咬人,許多人想辦法想對 付牠,曾經想把牠毒死,卻功虧一簣,呈現出黑色喜劇的況味。瑪格斯死後,敘述者在木板上用拉丁文刻下墓誌銘Cave Canem(當心惡犬),也算是最好的紀念了。
- 一連串的錯誤事件
〈追想大學時〉和〈我在徵兵委員會的夜晚〉則是以敘述者本身的眼疾作為起點,描述自己在大學課堂生活,以及在兵役體檢 中心所發生的趣事(或悲劇)。眼疾本身使敘述者在特定環境中顯得格格不入,在〈追想大學時〉中,植物學老師想讓敘述者「看到植物的細胞,否則這輩子就不教 書了」,但礙於敘述者的視力問題和態度(「不管怎麼說,這種觀察方式都有損於花的美感」),植物學老師的努力終告失敗。上軍訓課時,他也是唯一一位上了大 四還在穿軍訓制服的學生。整體而言,瑟伯以眼疾出發,帶出一般個人在教育環境中的問題:植物學和經濟學的兩門課讓敘述者「痛苦萬分」,體育課讓敘述者「生 不如死」,而軍訓課讓他知道自己是「這間學校最大的問題」。
〈我在徵兵委員會的夜晚〉描述敘述者一九一八年六月離開了大學之後,因兵役問題而到體檢中心報到。故事前半部說明爺爺 年紀一大把了還想為國服務,但就是收不到徵集令。相反的,敘述者儘管視力有問題,不用當兵,卻因行政上一連串的疏失,不斷收到體檢中心的複檢通知單,就算 告訴醫生自己早已被刷掉,也沒人相信。因視力受損之故,敘述者告訴醫生,在他眼中他「不過是一團黑影」(You're just a blur to me),然而,醫生會錯意,則回嗆說道:「在我眼裡,你什麼也不是。」(You're absolutely nothing to me)一語雙關的高段幽默,立刻讓擾民悲劇成為最佳喜劇素材,後來,敘述者甚至因為碰巧拾起桌上聽診器,突然被當成負責體檢的醫生,還一連服務了四個月。 除了荒謬,還是荒謬。最後,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他的兵役問題才總算自動消失了。
我們不難發現瑟伯喜歡製造故事的效/笑果。在他的手上,每一篇故事都將一系列的事件堆疊到一定的混亂程度,最後劇情直 轉急下,嘎然而止,(新)秩序於焉誕生。這種寫作方式就是「瑟伯氏幽默感」的最佳實踐:幽默感是一種「情緒上的混沌狀態」(an emotional chaos)。
儘管過世近六十年,瑟伯的作品依舊為這個世界帶來不少笑聲與深刻的思考。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說,凡是可以提供我們思想泉源的作家就可以被視為「我們的當代人」(our contemporaries)。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儘管年代有點久遠,瑟伯依然是「我們的當代人」,是永遠不退流行的「大幽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