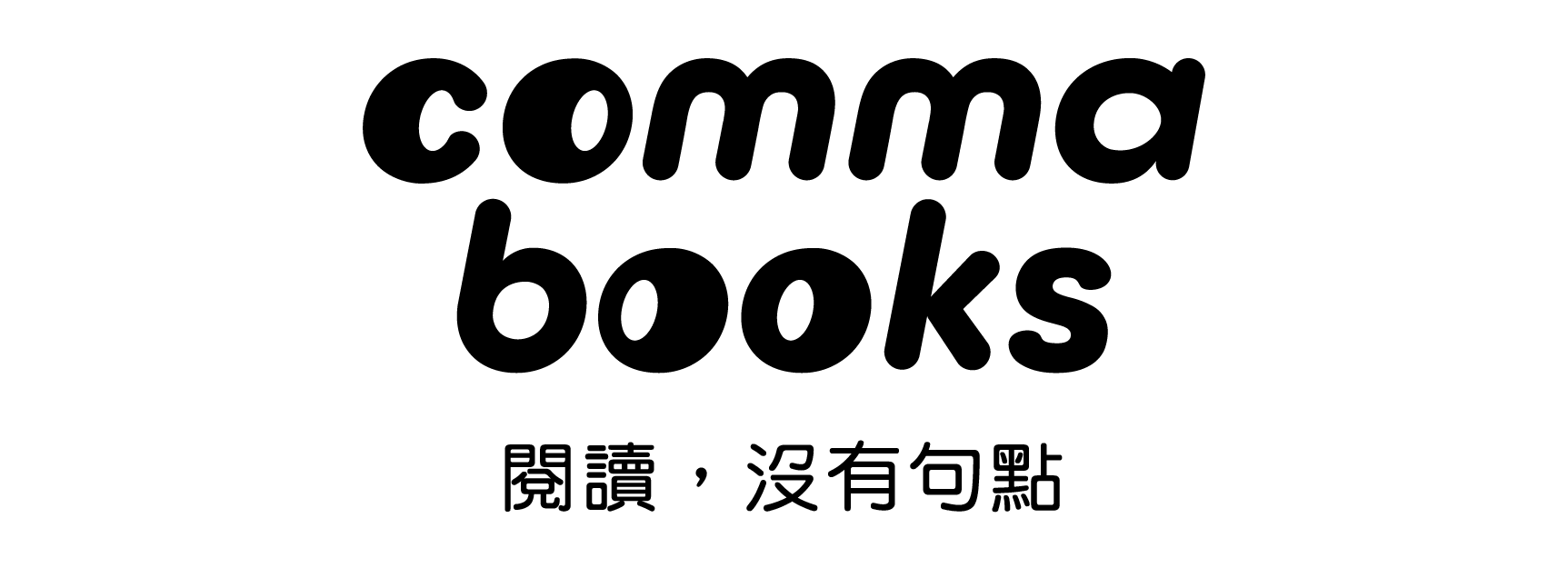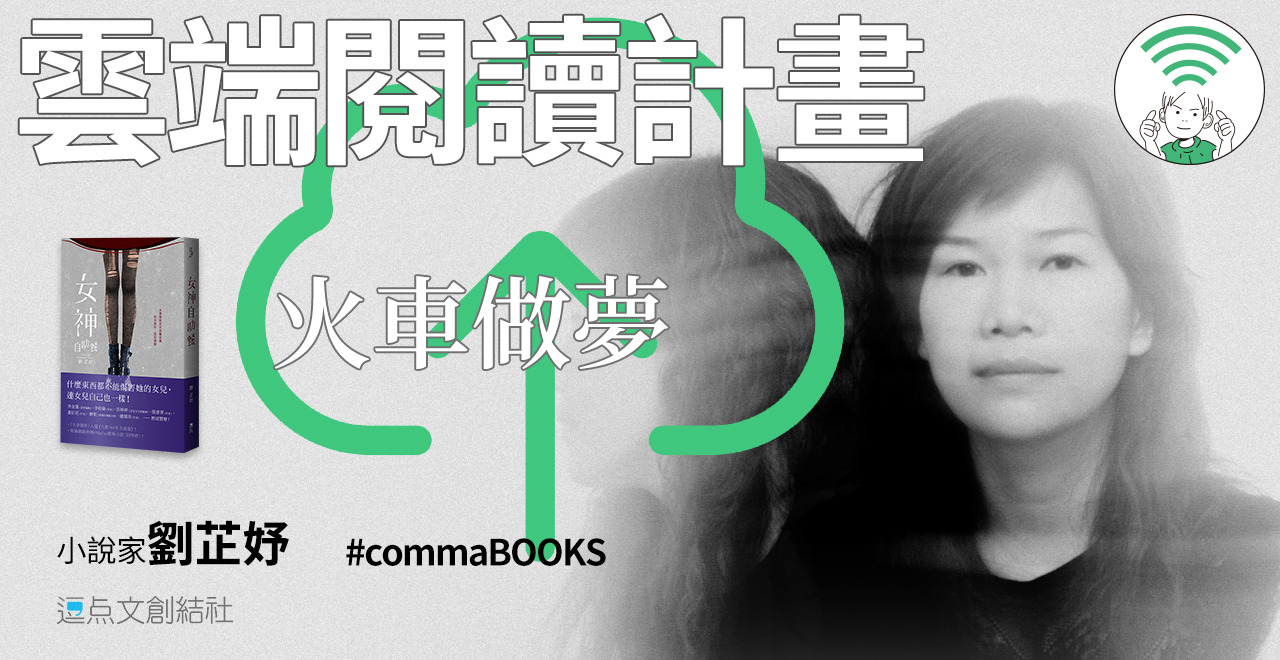
劉芷妤《女神自助餐》〈火車做夢〉
這班花蓮往臺北的快車上,她左右臂各彎了一個提袋,左肩疊了兩個包的背帶,右耳與右肩挾持人質般夾著行動電話,用一種身上扛著幾十條人命的女武神之姿,義無反顧地疾步往花蓮,也就是車尾的方向而去。宏觀看來,那奔向來處的徒勞,幾乎有種神話般的美感。
「喂?喂?講話啊喂⋯⋯聽得到嗎?喂喂?搞什麼這電話一點用也沒有,喂?喂?有沒有聽到⋯⋯啊我平常每個月付你二八八是在付假的?喂⋯⋯」
車廂裡每個位置都坐著人,寥寥幾個站客,也心照不宣地彼此拉開一段距離,各自斜倚在某個靠走道的椅背上,在這昏懶的午後時光,多數人不是閉著眼小睡,就是眼神渙散,在疾馳的絕對動態中,懨成絕對的靜態。
此刻他們全醒了。一個一個,骨牌似的,方向一致地轉頭,將如出一轍的嫌惡表情,長矛般擲向她沿路罵罵咧咧的背影,可惜連背影他們也看不久,她很快地消失在他們的視線之中,帶著一種誰准你看我的車尾燈了的氣魄。
她離開以後,車廂內重新回到可喜的靜態。骨牌們一一轉回原位,帶著自覺的優雅,與必須的碎聲公評。
「有夠沒水準,全身贅肉都在抖還有臉把全車吵醒,那種歐巴桑真的是沒救,這裡收不到訊號不是常識嗎?」
「我覺得剛剛被強姦了兩次,一次是視覺強姦一次是聽覺強姦,可以申請國賠嗎?我也有#metoo可以寫了!」
列車搖搖晃晃,貼著溽夏時節長滿濃綠蕨類的潮濕山壁行駛,不知道是不是正在山坳間行進的關係,車廂裡聽見的火車聲音非常大,行駛的巨響在山壁與車廂間碰撞迴盪,響得似乎可以吃掉世界上任何其他聲音,吃掉音量節制的嗤笑,吃掉知書達禮的白眼,吃掉整個世界都站在我這邊的真沒辦法。
那白噪音極大,而且不知饜足,一直吃一直吃,吃得更大,更白,白得幾乎發亮。
轟隆,轟隆。
她一路逆著車行方向走,過了不知幾個車廂,終於放棄原先找個收訊好的角落講電話的念頭。女兒教過她要看行動電話左上角顯示的訊號強弱,而此刻那裡只寫著她的老花眼幾乎看不清的「沒有服務」。
一輩子也沒有要行動電話服務過幾次,真的需要的時候就客客氣氣冷冷淡淡跟你說沒有服務了。活到這年歲早知道人生就是這麼棘歪,但還是真的很不爽。
電話彼端是女兒啊。 幾站前在另一個車廂裡睡得正酣時被叫醒了,有個年輕人亮出車票說這是他女朋友的位置,要她讓座。她根本看不清楚年輕人在她眼前晃來晃去的車票,但很確定自己的車票沒有錯,那可是在花蓮站窗口買票時有嘴講到沒涎才終於拗到票務員賣給她的臺鐵員工保留座,哪有可能讓?她也掏出車票,學年輕人在他眼前揮舞,同時好好講了一遍敬老尊賢尊敬長輩等等做人處事的大道理,結果眼前這頭髮染得和自己同款灰的屁孩一臉「就知道妳會這樣」的不屑表情,跟他的女朋友拿出行動電話開始對著她錄影,一邊錄一邊說什麼不是老了就值得尊敬啦妳會死我會大啦,躲在鏡頭後的表情,跟女兒罵她正義魔人自私大媽時一模一樣。
正想罵人,女兒的電話就來了。哎喲這查某囡,一定是後悔叫我回臺北了。她手忙腳亂趕緊接起電話,喂了半天也沒聽見那頭有什麼聲音,以為女兒正在哭,哭得說不出話,趕緊連聲安撫說是不是想媽媽了我下一站就落車搭下一班車回去,一邊講一邊下意識地往外走想找個收訊好的地方,然後才發現電話那頭不知何時早已掛斷,而剛剛的位置,已經被灰髮屁孩的女友坐走,還嫌歐巴桑的屁股把坐墊弄得好熱好噁心。
列車過彎,飄撇地甩了一個尾,她晃了一晃,手上的行動電話沒拿穩飛了出去,她趕緊撿了回來,確認沒壞,抬起頭已經半個車廂的人都在看她。
算了反正下一站就要落車,先搞清楚女兒到底要跟她說什麼比較重要。她一語不發,臭臉擠進窄仄的卡座裡,拿走自己放在行李架上的大包小包,故意用包包去撞了幾下那兩個屁孩,這之中,一直有鏡頭對著她。
扛起行李她開始往後方車廂走,回撥不斷失敗,她開始煩惱會不會出了什麼事呢?不會的醫生護士都在照顧她,那到底為什麼不接電話?剛剛還打給她的。
那白噪音,吃掉一切聲響的白噪音,也在吃她的女兒嗎?
轟隆,轟隆。
終於放棄撥電話時,她已經抵達最後一節車廂,座位仍是滿的,她默默找了個椅背靠著,那位置坐著的中年女人跳起來說阿姨這讓妳坐吧,她連忙搖手拒絕,心裡咋舌:拜託叫什麼阿姨,妳這年紀也不會比我小幾歲,還輪不到妳來給我讓座吼。
為了避免尷尬,她又往車尾移動了幾步。把提袋背包都找了塊空著的行李架丟上去,靠上另一個椅背時,小心不驚醒那個位置的乘客。
折騰一陣,她又睏了。從年輕時她便是上車就睡的類型,火車上的搖晃與轟隆聲響完全是催眠神器,況且這列火車聲音特別大,開起來特別晃,弄得她好想睡。
年輕時帶著女兒搭車,女兒最喜歡的不是窗外的風景,而是入夜後或隧道裡,鏡像化的窗玻璃。常常她睡得迷迷糊糊在不知身何處的車上醒來,第一眼看見的就是女兒晶亮亮地盯著黑色的窗,窗外明明什麼都看不見,只有遠處燈火與車內微光交疊成搖晃的亮點,母女倆與其他乘客的臉,像畫了一半就擱下的素描,在黑色鏡面影影綽綽地閃現。
女兒說,那是火車的夢。火車做夢好好看,所以捨不得睡。
醫院裡的護士會在睡覺時間放火車、海浪、冷氣運轉聲或樹林裡的風聲給女兒聽,她就是從護士那裡學到什麼叫白噪音的,白噪音可以幫助入睡,難怪她在火車裡老是這麼好睡,原來是因為白噪音的關係。
啊不對,不能說護士,要說護理師,女兒講過她好幾次,她老是忘記。
可是,不管在醫院裡或火車上,她迅速地入睡以後,女兒都在做什麼呢?在她身邊,卻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嗎? 如果她的好睡能分一點給總是失眠的女兒就好了,她想。這樣不知道能省多少安眠藥。
轟隆,轟隆。
這列從花蓮上行的火車窗景,從一開始的滿眼海天湛藍,變成如今潮濕山城的蕨葉濃綠,那綠純正得像是剛從生產線上做好,準備運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再拿來稀釋重製成其他綠色物件的濃縮原汁。她想起女兒每天早上要她吃的葉黃素,覺得窗外這綠對眼睛的益處大約也是十倍於別處的綠,索性認真盯看起來。
車窗邊的人大多睡著了,剛剛在海岸段拉起來擋太陽的簾布遮住了大半的窗景,她又想起女兒對她的冷眼,好不容易忍住探身去拉開別人座位邊窗簾的衝動,只得有點委屈地盯著沒拉實的簾布間透出的那點狹長窗玻璃看。高速行駛間,窗外所有細節都退隱江湖,只剩棕黑墨綠啞黃麻灰這些大小色塊,不停從玻璃上飛掠,看久了像是萬花筒,反倒讓她更想睡了。 哎呀再撐會兒,不能睡著,下一站要記得落車,給女兒打電話。
轟隆,轟隆。
列車進入山洞,這段路多的是山洞,每一個都不長,卻非常密集,明暗間隔短暫,交替得瑣碎而頻繁。剛從滿眼綠進入隧道的那瞬間,她總想到女兒,女兒每次往返花蓮臺北,經過這段時,不知還愛不愛看火車做夢?這樣的夢亂七八糟的一下子就醒了,醒沒多久又掉進另一個夢裡,那多不舒服啊,可是醫生說女兒就是長期在這樣的軌道上,自己一個人跑著。
這是什麼軌道?這也算是軌道?軌道不就是安安穩穩過日子嗎,正常人怎麼會受得了這種起起落落?爸爸媽媽辛辛苦苦賺錢把妳送到花蓮念研究所,包吃包住包念書包玩樂,結果妳在那裡憂鬱症還是躁鬱症,這樣哪裡有對?妳是有什麼好憂鬱的?不愁吃穿有什麼好尋死尋活?
女兒從來不回答她的這些問題,總臭著臉,就像現在黑亮的窗玻璃上映著的那個年輕女孩子的側面,明明五官乾淨漂亮,映在窗上的鼻樑下巴眼睛嘴脣都線條明晰,但就是一副全世界都欠她會錢的樣子。這些小女生哪裡知道什麼叫做欠會錢被倒會?一天到晚臭著張臉,醫院裡的護士跟她說這是年輕人流行的厭世,什麼厭世?都還沒出社會,連世界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說什麼厭世。
轟隆,轟隆。
列車出了山洞,有益養生的濃綠再度回到玻璃上,她趕忙又盯著看,想著每天早上陪女兒一起吃藥時吃的葉黃素,為什麼叫葉黃素呢?不都說多看綠色才對眼睛好嗎?還有那個花青素,花怎麼就青了呢?
青了的,是她那天接到電話,聽見學校說女兒自殺被發現緊急送醫的那張臉。臉青著時間停著,但奇怪的是手上的鍋鏟還在煎盤上俐落切著蛋餅,好像人跟身體真的可以分開似的,煎盤邊緣的隔熱板後站滿等著早餐要趕去上班的客人,他們也都是那張不耐煩的厭世臉。
但他們沒有自殺。
她沒想過世界到底討不討人厭,就像沒想過為什麼葉子應該是綠的卻有葉黃素,花應該是紅的粉的紫的黃的但偏偏有個花青素,噪音摸都摸不到可是竟然有白色的。
轟隆,轟隆。
綠沒幾秒鐘,火車又進山洞了。窗玻璃上這次映出來的是一張男人的笑,奇怪剛剛不是一個臭臉妹仔嗎?她眨眨眼,再認真看一次,沒錯,是個男人的笑,但不知道為什麼,她就是覺得那笑容很討厭。
實在了然,要嘛厭世,要嘛連笑都討人厭,現在的人到底都有什麼問題?她記起常常有客人跟她說,阿姨,看到妳的陽光笑容就覺得整個早上都充滿活力了。忍不住對著空氣咧出自己引以為傲的飽滿笑容,摸摸臉頰拉扯的弧度確認這技能尚未生疏。
為什麼這些都遺傳不到女兒身上呢?
轟隆,轟隆。
這段路好多山洞,窗玻璃亮了又暗,綠了又黑,這次出現的是一開始看到那個臭臉妹仔,妹仔表情比第一次看到時還難看,白白浪費了一張水姑娘的臉蛋。
這妹仔的爸爸媽媽恐怕也跟自己一樣不知道該拿女兒怎麼辦吧。她掏出口袋裡的行動電話又看一眼,沒有服務。
轟隆,轟隆。
男人的笑。
轟隆,轟隆。
妹仔臭臉。
轟隆,轟隆。
男人的笑。
轟隆,轟隆。
奇怪,為什麼同一塊玻璃上映出來的臉,每次過山洞時看到的會不一樣?像是這深山的隧道裡有什麼魔神仔在跟她開玩笑似的,又像是某種囝仔的塑膠玩具娃娃,按一下頭,就會換一張臉。咔啦咔啦,喜怒哀樂,咔啦咔啦,表情都不一樣。 若像是女兒講的火車做夢,難道是這輛火車做惡夢了?還是她在女兒的病房待太久,被隔壁病房那個愛撞牆的傳染了神經病?
這種話講出來一定會被女兒罵,說她政治不正確,然後呢她跟女兒講什麼人生道理要開導伊,又被說是太正面太政治正確。真的是吼,什麼都乎伊講就好了。 在病房裡,她也的確是什麼都讓乎伊。女兒說自己吃藥很無聊,她就陪著吃維他命葉黃素;女兒說媽你回去工作啦每天在這裡我壓力很大,她就收了東西回臺北,假裝自己狠得下心,可以把女兒留在那幢高樓的其中一個病房裡。
她什麼都依了這個查某囝,但怎麼樣就是問不出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什麼事要弄到自殺。醫生叫她不要問了,她也就不敢問了。這年頭,做媽媽的問個問題還會被醫生罵。
她有好多問題想問,可是她不敢問,女兒不想答,她們的聲音,像是都給白噪音吃光光了。
轟隆,轟隆。
這次,窗玻璃映著的妹仔的臉,臭得像是已經快要哭出來了。
她終於忍不住轉過身,想要搞清楚到底那個玻璃上映著的是男是女,還是魔神仔。車廂裡大部分的人都在睡覺,就算醒著,低頭盯著行動電話的樣子也像是進入另一種睡眠狀態,她眼光掃了一圈,很快就找到其中一個卡座上,明顯和其他乘客動作不同的那對男女。
因為被成列椅背與乘客擋住,從她的角度,只看得到那個掛著笑的男人,一隻手抓著臭臉妹仔的肩頭,試圖將妹仔拉往自己,臭臉妹仔不斷躲著男人湊過來的臉啊手啊身體啊,男人又不斷靠上去。不知為什麼,或許是因為列車的轟隆巨響實在太大,晃動也太劇烈,這場隱藏在兩個座位間情緒飽滿的小小追逐戰,竟和她在窗玻璃上看見的倒影同樣無聲。妹仔微弱的抵抗並沒有超出那個卡座的範圍,也沒有驚動任何睡著或醒著的乘客,只讓他們的臉在拉扯之間,前前後後地,交替出現在她盯著的那塊小小窗景上。
滿座的車廂裡,像是只有他們三個人知道這件事,其他人的視線都垂得低低的,不知道是沒看到還是不想看到,而她竟也下意識地轉回原來的姿勢,想把自己藏進「不知道這件事」的多數裡。
然而她畢竟是知道了。
轟隆,轟隆。
回到同樣的姿態角度,她不可避免地在火車進山洞時,又看見那塊窗玻璃倒映著的男人的笑。現在她知道為什麼這男人笑起來這麼討人厭了,可是那妹仔要真的碰到什麼性騷擾還是怪叔叔,幹嘛不喊大聲一點呢?不然站起來直接離開那個位置也可以啊。搞不好他們是情侶,說不定她多管閒事過去問兩句,還會被罵回來,而且要是被那個男的打怎麼辦,這車廂裡看起來沒有人會救她。
嗐,這就是那個妹仔不對了,若是真的遇到壞人就要喊啊,都不會喊,動作又那麼小,是有誰會知道要怎麼幫忙?
她想起女兒說她正義魔人,要她小心點,說現在大家都有行動電話,隨時都會有人把你當正義魔人的嘴臉錄下來,上傳網路。 她是不知道正義和網路的關係到底是什麼啦,在網路上,正義就會更正義一點嗎?火車轟隆轟隆駛進下一個山洞,當她從窗玻璃又看到妹仔的臭臉,跟女兒一樣臭的那張臉,她突然想起很久以前,可能有十幾年了的那種很久以前,她也曾經在同樣的火車場景裡,看著另一個妹仔,臉上露出同樣的表情。
那時候,她還太年輕,不知道自己能夠做什麼,可是有另一個人走過去說話了。記憶裡那遙遠時空中,每個人的面目都已經模糊,她卻還記得那個人走過去的時候說了什麼話,那個聲音清晰脆亮,好像此刻才剛在耳邊響起,好像山洞與火車之間彷彿可以吞吃一切的白噪音,一點都干擾不了那個聲音。 她再看了一眼那個妹仔倒映在窗玻璃上的臉,依稀記起,十幾年前的十幾年前,在自己當妹仔的時候,有幾次,也曾經露出這種表情。
她的女兒也露出過那種表情嗎?那時候,有沒有一個聲音,冒著成為正義魔人的風險去幫忙女兒?如果有那樣的聲音,如果有,女兒是不是此刻就不會在醫院裡?
轟隆,轟隆。
火車出了山洞,她轉過身,走向那個卡座。 她瞥了一眼男人,男人很快收回放在妹仔身上的手,戒備地看著她。
「小姐,這個座位是我的,妳可以把位置還給我嗎?」十幾年前那個清晰脆亮的聲音,從她的嘴裡吐出,與窗外的亮綠一樣晶瑩。
妹仔微微仰頭,整個人都傻了,只能用那雙快哭出來的水汪汪眼睛看著她,瞬乎變換幾千種表情,每一種表情裡肯定都浸潤了飽滿的感激。
「可是,阿桑,這是我的位置耶,你看,號碼是一樣的⋯⋯」妹仔從身上摸出對號車票。
阿桑你個頭啦。她氣死了,整個肚腹裡燃起大火。妳老母辛辛苦苦每天天沒亮就起床備料做早餐做了二三十年,衣服捨不得多買一件,把錢都給妳去念研究所,妳給我念成這樣!了然!書都讀到屁股去了,妳笨成這樣妳媽知道嗎?這社會交給你們這種年輕人不如給阿共打下來算了!
「幹伊蛤仔,我真的會被氣死,拎祖媽叫妳站起來啦,我愛睏得半死讓老人家坐一下會怎麼樣?你們這些年輕人真的是很不知好歹,大人教的都沒有在聽,尊師重道啦敬老尊賢啦都不會,年紀輕輕站一下好像要妳的命一樣,等一下就到臺北了啦毋免妳站很久啦,我剛剛站在那邊腳腿都麻了,是不能給我坐一下是不是?」
她拉高的嗓門吸引了周遭乘客的目光,細碎的議論聲被火車的巨響高速輾成粉塵,還有人拿出行動電話,用鏡頭對著她,奇怪吶,剛剛真的該錄影存證的時候這些人都死哪裡去了。
「喔,好啦,阿桑那這裡給你坐。」妹仔諾諾起身,離開了那個現場,男人一句也沒吭,看來是真的互不認識的兩人。
她裝作毫不客氣地,一屁股坐在還留有妹仔體溫的絨布座位上,眼角餘光發現男人還在看她,她有點緊張,壯起膽子瞪了回去,在男人下意識轉開眼睛的那空檔,趕緊把外套拉起來蓋住頭裝睡。
怎麼可能睡得著?緊張死了。大家都在看這裡有夠見笑,不過,那個男的應該不敢再騷擾妹仔了,也不知道這男的會不會對自己怎樣,實在垃圾,害她終於有位置睡覺了又不敢睡。
她想把行動電話再拿出來確認一次,看能不能撥通了,可是,她還不太敢動。那個男的最好也不敢動,大家就都不要動。
隔著蒙住頭的外套,好像聽見有人在罵她老番顛,但火車聲音太大,輕易輾過了那些難以聽清的不滿。她想著,回到病房要跟女兒說這件事,人生真的不用太在乎別人說什麼,他們連性騷擾都假裝看不到,連罵阿桑都只敢躲遠遠的碎念,那種人的意見有什麼好考慮的。
轟隆,轟隆。
不知道是不是列車的白噪音太強大,前一刻還緊張得要死的她,竟然真的睡著了。轟隆,轟隆。火車車廂真是全世界最適合睡覺的地方了,她夢見女兒回到小小一丁點的那時候,穿著她小時候最喜歡的那件綠色洋裝,小狗一樣趴在窗邊看火車做夢;咻地一下從溜滑梯滑下來,蝴蝶一樣在她的腳邊繞來繞去地飛,飛啊飛啊,那揚起的裙襬美得像行過山城時,她在火車的窗玻璃上看到的那樣,是用最純正新鮮的原料製成,一點也沒有摻水。
那是多好的年紀啊。那時候,什麼東西都不能傷害她的女兒,連女兒自己也一樣。
轟隆,轟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