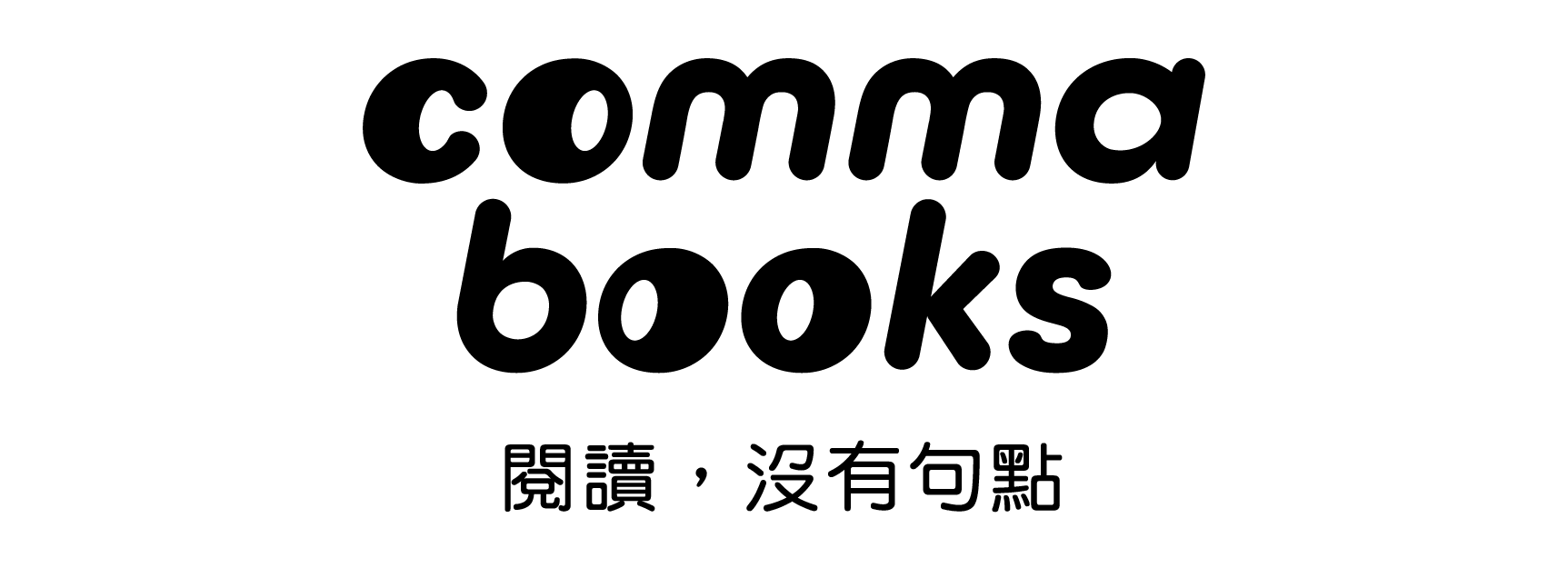又仁《我娘》三篇:〈 學著當媽媽 〉、 〈 基努李維 〉、 〈獨角戲 〉
〈學著當媽媽〉
長大後發現,媽媽對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有著各種矛盾,現在想起,對於她的這些矛盾,充滿心疼。
像是她對我們在課業上的要求,許多成分或許來自於鄰居與親戚之間的比較,叛逆的中學時期我會特別點出「比較心態」回嘴,當然、一位天秤座媽媽在氣頭上聽到「頂嘴」只會更加爆炸,下一步就是上演將我的參考書或練習測驗卷丟入垃圾桶的戲碼,等氣消了會撿回來告訴我說媽媽都是為我好。我想許多爸媽也是如此,將期望放在小孩的課業上,另一方面就是壓力。但她打從心底,真的這麼在乎課業上的「分數」嗎?或者也是周遭各方耳語帶來的壓力?後來我和老妹都走上戲劇路,媽媽和老爸北上來看我每一場演出,似乎代表她終於放下了那些標準與限制。可能是大學後我們都離家,她管不著了,或許覺得小孩沒學壞就好,也可能回想過去對我們的要求,像是她在守住某種自己設下的底線;又或者是如今,我們都更認識彼此了。
另一種矛盾,是在我幼稚園大班時發現的。
幼稚園時她總是每天早上騎著機車載我到學校後,再開張家中客廳的家庭髮廊。但那一天我清晰記得,雨下得很大,機車被老爸騎去警局上班,她盡快將我套上一件輕便雨衣,牽著我和老妹到隔壁,將老妹暫時託給張太太後借了機車。張太太是媽媽的常客,來做頭髮時會跟著爸媽一樣叫我的小名「涂寶」,記得我小時很愛模仿她高亢親切的語調說話,我媽就會笑到東倒西歪。
跳上機車後座,媽要我緊抱她,迅速將身穿的大件桃紅色雨衣一大塊包覆住我的頭,不讓迎風射過來的支支雨點往我臉上來。那段路我被整片桃紅包圍,伴著媽媽熟悉的香水味。桃紅之外的世界蒙著一層悶悶的不斷掃過的唰唰雨聲,聲響越來越密集、節拍越來越快,交雜各種人車聲嗡嗡地出現又瞬間閃逝,當時媽媽肯定被時間逼得焦躁。
在心理時間預測快到學校時,突然一個強力停頓,擺動,將我用力往後甩動又大力彈回,碰一聲撞上老媽的背部。聽見一聲尖銳的女人喊叫後,整片桃紅世界往左下方傾斜,我頭上安全帽先碰到一面牆,力道不算太大,到左腳小腿肚內側有擠壓的力道襲來,帶點灼熱讓我下意識立刻抽出。我才發現那是柏油路,不是牆,我是躺著的,剛剛是她的喊叫聲,機車是不是倒了?我才迅速鑽出那片桃紅,媽媽側躺在我眼前,安全帽依然在頭上,旁邊的雨聲和人車聲變得尖銳清晰。我緩緩抬起頭才看見,四周許多人圍上,前方停著一輛藍色小貨車,視線掃回倒下的機車,後照鏡都碎裂了,啊,車禍,是我們自己出車禍了,媽媽!愣了一小段時間,才開始搖晃我媽,只覺得剛剛的一切都是慢動作。剛好左方對面有間醫院,對,我已經快到幼稚園了,那是學校附近的醫院欸,我當時這樣想。很快地,有幾位穿著白衣的人衝向我們,還有人推著一張有滾輪的床,又有人將我扶起,一切才從慢速轉回正常。
後來我就坐在病房中了。記得護士一邊幫我擦藥一邊說好在只有小腿擦傷,沒多久,媽醒來了。周圍除了醫護人員,爸也趕來了,似乎還有一位中年男子大概是小貨車司機,我的大班導師和園長也來了。我怎麼在醫院?媽醒來後開始問問題,爸爸簡單回覆也要她不要擔心。涂寶呢?我立刻湊上前讓媽媽看見我。妹妹呢?爸爸回說妹妹在張太太家,要她放心。但那時我已經知道怪了,果然沒五分鐘,媽媽開始重複這些問題,又問到我時,我立刻抓著她的手告訴她:我在這裡。心裡開始慌,園長先將我帶往學校。
想必已過中午,周圍沒有時鐘,園長先帶我到學校的廚房,她陪我坐在廚房某個角落吃飯,廚房阿姨們已經開始收拾各班的大型餐具。那天吃的是我最愛的炒飯,一如往常吃了兩盤以上,園長笑我很會吃,這樣很好。而我一邊扒著飯一邊沒忘媽媽的狀況而開始問園長,她只要我別擔心,說媽媽沒事。左小腿上的擦傷提醒著,刺刺的。
過兩天後媽媽回來了,那幾天爸爸都沒去上班,在家陪她,跟著媽在家裡外走來走去,媽媽一樣重複各種問題,大多是生活上的瑣事或是我和妹妹在哪裡之類的。我下課回到家只敢偷偷在一旁看著,寫功課也看,洗完澡也會在房間偷聽,一心很怕媽媽會不會哪天忘記我們。
某天晚上,媽媽一個人走到陽臺紗門前,小心翼翼地左顧右盼像在找什麼,像是對眼前的一切充滿陌生,爸爸沒一會出現問她要不要出去陽臺吹吹風,媽突然探了一下陽臺方向說,很暗。媽媽怕暗嗎?我當時跳出這想法,偷偷在房間望著爸媽的一舉一動,爸爸立刻安慰說,放心、陽臺有小燈。
原來媽媽也怕黑。
比較大了之後,才知道當時媽媽因為在小貨車後方的那一下撞擊,導致腦部有些微的出血並結塊,因而產生選擇性忘記事情、問了又忘的症狀,大概經過兩週的治療後就復原了。
原來媽媽怕黑,這是那時很大的衝擊。因為媽常在晚上要我們到陽臺幫忙洗衣或晾衣,我總會喊著好暗好暗,她總是回說怕什麼,又沒有東西會把你吃掉,然後我就回答誰叫妳都騙人說有虎姑婆。更大了之後,媽也跟我承認她怕黑、怕蛇、怕走在小巷子裡。
直到有天我明白了,所有的口是心非與矛盾,是為了孩子端出的逞強,或說是她慢慢長出的勇敢,更是她在我們成長的路上從未停止學著,如何當媽媽。
〈基努李維〉
斗六有一家「雙子星戲院」,許多雲林人都不陌生。我們總會打電話過去,聽著熟悉的中年男子以親切的臺灣國語口音,播報當日電影時刻表,可能是經營這家戲院的阿伯自己錄製的,戲院由他經營,也兼撕票和播放電影,這是許多雲林人的共同回憶。
記得一家人在那裡觀賞過《鐵達尼號》、《酷斯拉》,和幾部柯南動畫電影版系列。只要爸放假,媽的髮廊傍晚後休息,一家四口就迎著晚風,「四貼」緊抱著乘坐機車前往戲院看電影,那是至今最興奮難忘的時刻。時代變遷後,雙子星轉為二輪戲院,另一家首輪電影院中華影城來到斗六,雙子星戲院在七八年前也走入歷史,中華影城在二十年前成了我們衝首輪電影的據點。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中華影城觀賞了《駭客任務》。二零一九年七月因為電影二十週年,復刻上映,讓我想起了一九九九年的那天午後。
兩個多小時的震撼後走出戲院,留在腦中的除了經典又令人瞠目結舌的三百六十度凝結畫面、基努李維下腰躲子彈的慢動作鏡頭,對我來說,少不了他的英俊形象,怎麼可以這麼帥啊。
離開戲院到回家的路程很短,但身體與心理莫名起了奇妙變化,想到基努李維在電影中的各樣狀態,開始不自覺發燙,下半身甚至有些反應。回到家後,我對爸媽說想回房睡午覺,其實撒了謊。我立刻鎖上房門,也將對內的那扇窗緊閉上鎖。打開電腦,等著撥接上網的吱吱聲響,焦躁了起來,當時覺得撥接上網也叫太久,太慢了吧。一連上網立刻在蕃薯藤或奇摩網站搜尋列上輸入「基努李維」,特地用原文再搜尋一遍,瀏覽關於他的各式資料和圖片,當下感受身體和心理的細微反應,某種興奮的灼熱、冒著汗,心跳在胸口更為清楚地拍打,延伸到下體的躁動。那時我不知道怎麼一回事,處在摸索身體即將邁入青春期的轉變期。
說實在,那時有點討厭我爸,也討厭自己。
在那之前的幾年,我都和妹妹一起睡,房間在二樓爸媽臥室隔壁。有天爸覺得我身為老大也是男生,得開始獨立,因此三樓裝潢整頓好後,被他邊罵邊趕上樓去了,那時邊哭邊要我媽幫忙求情,媽甚至有幾天看到我半夜偷偷跑下來找妹妹,特地幫我保密。當時的我膽小,剛搬上去的前幾天晚上,睡前總會躺在床上睜眼望著天花板許久。有次疑神疑鬼緊盯著床邊那扇對外窗,二到三樓的樓梯間有盞黃燈,讓窗外看起來充滿亮光,有個巨大影子突然閃過,讓我嚇到直接抓緊棉被飆出淚。等我爸出聲跟我道晚安後,才知道只是他來收衣服準備下樓的身影。
其實會說討厭爸,呼應到他的管教方式與「重女輕男」。相同事件若同時在我和妹妹身上發生,通常被打罵的都是我。像是看電視的時候,穿鞋的腳不要放到沙發上,若是妹妹,他就好聲好氣告訴她,換作是我,他會直接一個手掌用力往我大腿搧打上來。或許跟職業是警察有關吧,在我心中他一直是嚴厲的形象。很小的時候,曾在一次類似重女輕男的事件被爸打罵後,用注音寫了紙條——ㄨㄛˇ、ㄊㄠˇ、ㄧㄢˋ、ㄋㄧˇ,氣沖沖地丟在他的書桌上,因為如此,那天晚上在床上含著眼淚聽我媽念了好久。
回想起來,相信當時他心中必然很難過。現在覺得好在他逼著我上樓,只為了讓我能好好念書,整個家裡也只有我房間有電腦,這些都是沒說出口的愛的表達。另一方面,他或許不知道,他在我成長過程中,讓我意識到自己天生的許多不同,卻也讓當時的我多渴望能有個出口,關於那些生理與心理上的變化,讓我不帶畏懼地吐露這當中的無助、挫折與困惑。
這些結在多年前解開了,我依然想抱抱爸說一聲,我們都辛苦了。
喔,當然也要謝謝基努,但要抱到他,應該是不容易,哈。
〈獨角戲〉
二零一二年的夏天,每天在板橋的租屋處,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寫劇本,耳邊最放聽的歌就是蛋堡的〈過程〉。
那時二十二歲,準備升上戲劇系三年級。一樣過著打工、排練、參加徵選、接案演出、上課的日子。大約是那年四月,有天和臺藝戲劇系同學、學長姐、還有正就讀北藝戲劇系的妹妹,擠在租屋客廳中吃消夜,聊著聊著就聊出了一個演出計畫,決定在當屆的臺北藝穗節演出。湊足十個人,因應當年藝穗節第一次有了策展模式,我被推舉為策展人。我們分成兩組,一組五個人,觀眾可以購買一組連看五齣獨角戲,或是買套票看足兩組十齣獨角戲。後來定案,以「顏色」為出發、以「青春」為主題,各自選出中意的顏色來發展關於自己青春記憶的故事,抽籤後完成分組。大家不約而同地,決定挖掘關於失去和遺憾的過往。
而我,選擇了最喜歡的藍色。
對我來說,表演具有療癒性,相信各領域的藝術創作者都會有同樣的體悟,創作本身就是和自己,也是和生活對話、碰撞的過程。演員也是創作者,同樣是茱麗葉,不同演員就會有不同的詮釋,來自演員身上所擁有的條件、特質、生命經歷,進而創造出各自的茱麗葉。而我們也從完成角色的經歷與生命過程裡,獲得成長,甚至更瞭解自己一些。這也是為什麼,過了幾年後再回來演同一個角色,又會有不一樣的角度和細節。
那是我的第一齣獨角戲演出,每個人有二十到二十五分鐘的時間,專注在一個事件和主題創作演出,已經非常足夠,但最初的挖掘是最難的。
當時的租處房東,是北藝大的兼任老師。當時看上那間老公寓,就是因為每一面牆都是一幅畫,其中一面藍色的牆就是仿米羅的〈藍色二號〉。那幅畫給了我很大的靈感,到現在也一直相信,當時碰到那個住所似乎早已註定,將創作出這齣小戲。
十個人的青春,就像十幅畫作,在空間裡的每個角落輪番上演,觀眾能在一百分鐘內移動到五個角落並且停留,也像在看展。
在創作前期,我查了資料顯示「男生藍色、女生粉紅」的色彩性別框架,是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以及製造業再度興起有關,顏色區別被拿來作為某種行銷的手段。最初,藍色給人溫柔、平靜的感受,在二戰前被視作女性的顏色。因此當時也有人稱同性戀為「Blue」。
我將這樣的色彩與歷史放進了我的劇本和舞臺上,開場觀眾只看見舞臺上有一塊大大的女廁標誌,一顆圓型的頭,下半身有三角形作為裙子,幾何拼湊成的代表圖形,但整個圖形,是藍色的。開場後我從大型標誌的背板後蹦出來,穿著一整套深藍色短袖洋裝,戴著淺藍色妹妹頭短假髮、搭配淺藍色絲襪與一雙粉紅色高跟鞋。跳完舞後,開始述說著關於離家、關於初戀的故事。長久以來在劇場演過許多角色,那次是我第一次在舞臺上扮裝,創造出這位叫「虹彩妹妹」的角色。
「十八歲那年我在臺中念書,當時很流行無名小站,右下角的九宮格裡是最新造訪自己網誌的網友,如果你有買銀卡或金卡,就可以跟人家炫耀你可以看到更多來你網誌光顧的網友人員。」每次說到這裡,臺下觀眾就會產生共鳴地大笑。「我就是在上面認識了我的初戀。那時候沒什麼錢,每到週末還是堅持買一張莒光號車票,從臺中一路叩叩叩到屏東找他,他大我一歲,正在念大二。記得第一次踏出車站門口,好忐忑好慌張,立刻拿起亞太,打去問他說:你在哪裡。接著看到十一點鐘方向,一個戴著白色安全帽、藍色口罩的男生,我知道,就是他。走過去跟他打了招呼,靦腆地說:你好。他竟然回:啊你本人怎麼這麼大隻。」觀眾再度哄堂大笑。
「記得那天風很涼,一坐上機車後座,他就出發準備帶我回他的租屋。一路上迎著南方的微風,忍不住盯著他脖子上的寒毛,我就突然很認真看著他的寒毛耶,當下覺得,怎麼會有人的寒毛隨風飄逸得這麼好看,身上還帶著一股很舒服的香味。那天之後,我們就正式在一起了。」
故事說到這邊,我總會先休息一下,跟觀眾玩問答遊戲。我會點一位臺下觀眾問:「一想到藍色,你會想到什麼?」其中一個場次,爸媽一如往常北上來觀賞。開演前,我難得緊張到發抖,不斷冒手汗。虹彩妹妹帶點特別的鄉音,交雜臺語,我希望她像觀眾們家隔壁的鄰居大姐、或是親切的親戚阿姨。除了是第一次以扮裝反串的模樣,在他們面前演出,最令我緊張的是,上述都是真實故事,透過虹彩妹妹說出來,也是我對他們隱藏多年的祕密,要說出來了。
到了互動的遊戲時間,透過虹彩妹妹,我鼓起勇氣指向爸爸。我的其他演出夥伴們,知道這場對我的重要性,演到這一段時,瞥見他們都在觀眾席後哭了,但我必須在角色裡,道出更深的故事。
演出結束後,我和妹妹陪著爸媽到臺北車站,回程前一起吃了晚餐。媽媽終於開口問我:「涂寶,剛剛演出的故事,都是真的嗎?」她複雜的心情在眼神中透露無疑。「嗯,百分之九十都是吧。」我眼淚即將奪眶。
「你快樂最重要啦,媽媽以前都覺得為什麼你總是選擇難走的路……」
「我沒有選擇啊。」
「我知道,我知道。後來我想想,對啊,我兒子沒有比別人差,也很優秀,我們真的很幸運了啊。」
「演得很好。」爸終於開口。
我努力含著眼淚,給了爸媽微笑,因為怕一開口,眼淚止不住。像往常一樣抱了抱爸媽,目送他們上月臺後,才在妹妹面前流下眼淚,我們兩個也擁抱著。
表演具有療癒性,必須挖掘自我,也在長期觀察他人、觀察自己的訓練中,同理各種角色,扮演和詮釋。最重要的是,把心打開,才能往前。就像十九歲那年某一天,在車站外跟爸媽道別,準備回北部排練,我鼓起了勇氣上前抱了他們,那是國中以後就沒有的親密接觸。我想跟他們和解,尤其是我爸,不想因為過去叛逆期與他們產生的各種不諒解,變成永久的疙瘩而沒有落幕的一天。那個擁抱,爸媽都嚇到了,媽甚至眼眶泛紅。肢體很奇妙,或許是東方教育的關係,讓我們總帶著對長輩的隔閡,爸媽在對待孩子的過程中也在學習,甚至沒有意識到縱向的對待,長時間下都在帶給彼此傷害。
那次過後,我們開始能將過去彼此給過的傷害、愧疚、誤解,像玩笑般地自然說出。我很開心主動做出這樣的改變,才能跟爸媽如同朋友一樣貼近,在二十二歲的獨角戲演出後,讓那些結,漸漸解開。
「離開世界之前,一切都是過程,活著不難,最難的是做人。」就像〈過程〉裡的歌詞,是啊,表演也一樣,人生更是,一輩子都學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