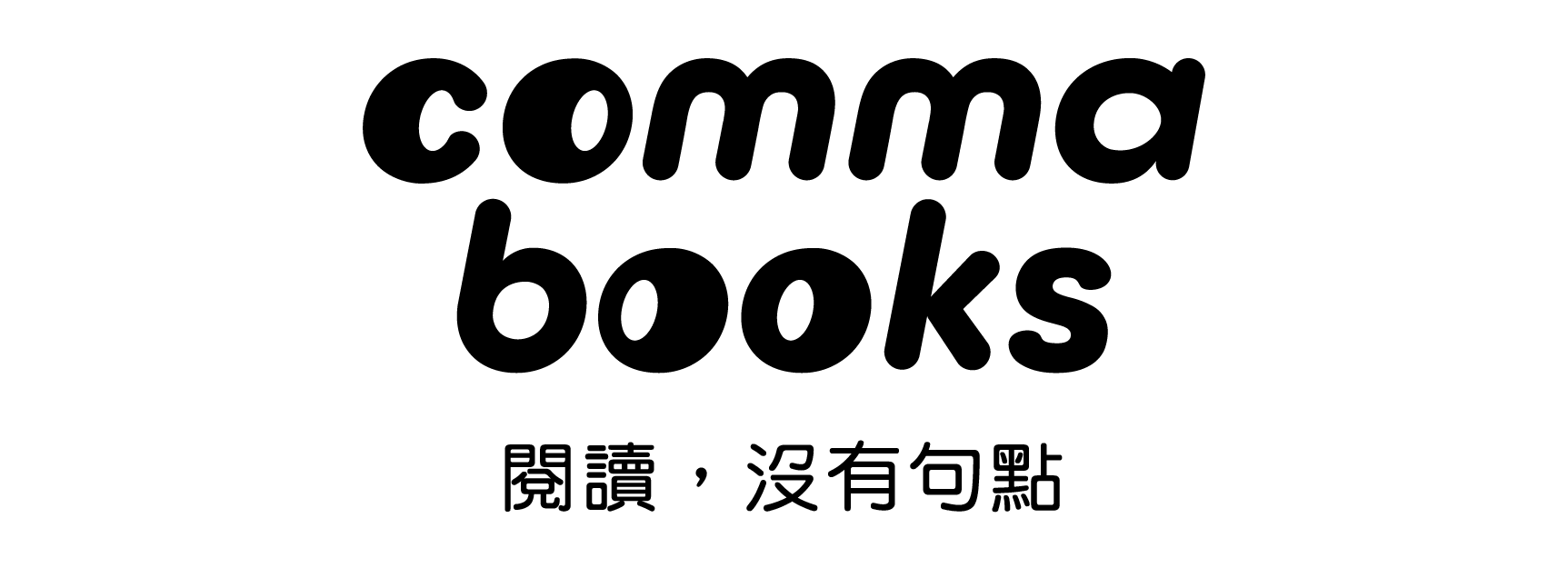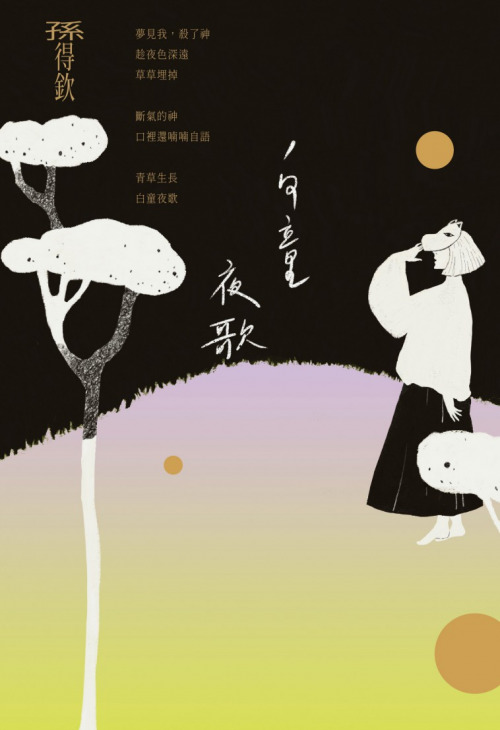「如果文學是救贖是力量,沒有道理越寫人生越糟吧。」——專訪《白童夜歌》孫得欽
一九八三年生的孫得欽,畢業於成功大學中文系、東華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著有詩集《有些影子怕黑》,參與黃以曦主導的多人對寫集《尤里西斯的狗》,譯有《當你來到幸福之海:卡比兒詩選》。
留著長髮、綁著一撮馬尾的孫得欽,給人一種在心中苦行(苦刑)的感覺,每次答覆都像是要從無邊大海裡撈出他所能給、最接近原意的語詞。那是一種靜靜的追求,即便孫得欽端坐於眼前,卻也有種他彷彿已經在遠行的怪奇印象。
《有些影子怕黑》出版於2014年,時隔六年多,當時以直擊愛、色情與青春記事備受矚目的孫得欽,在一切彷若暫時終止的2020年12月,帶來了與上一本詩集風格截然不同的《白童夜歌》——他為何轉變?又走過了什麼樣的人生體驗?
▉過往猶如前世,「我是一個普通的人」
專訪一開始請孫得欽談談原生家庭與求學時光,他露出了苦笑:「我對以前的事幾乎可以說是毫不在意,看到訪綱題目時,好像在回憶前世一樣,我盡量試試看。」
隨後,孫得欽帶著費力思索的神情,認真回應:「我長在一個很普通的家庭,爸爸做國貿,媽媽是會計和家管,我是成績好的乖乖牌學生,個性沉默內向,跟家人不是非常親密,總之是很普通的人,沒有發生什麼了不起的事。」孫得欽自言成長時期並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比如國、高中吹長笛,就只是因為笛子類的東西還算喜歡,要在家裡弄一架鋼琴又太難,而當時滿想要學會一種樂器,也就順理成章,其實並沒有特別的道理。
國小有印象的讀物是《孫叔叔說鬼故事》,國中是劉墉之類的課本作家,高中開始讀詩,也是從《新詩三百首》之類的入門,總而言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閱讀經驗,走一般大眾的方向。「最初讀詩,也是整個莫名其妙,完全看不懂。後來在某個文藝營,聽講師的解讀,才比較能夠感受到那些文字表達裡面的東西。真是很平凡的起點。」孫得欽這才開始寫詩發表於校刊,但也僅此而已。
大學就讀成功大學中文系的理由則是:「因為我只會這個,好像算是擅長而且也有興趣,很自然地就走上這個方向,並沒有刻意挑選。」孫得欽答覆提問時,如同在傾聽內在世界的聲音,予以確認後方才會做出謹小慎微的回應。
高中、大學時期寫詩的孫得欽,到了東華創英研究所,改弦易轍寫起短篇小說,原因是李永平的小說課,讓他徹底迷上短篇小說,比如說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的〈尋獲小舟〉(The Found Boat),好像稍微能觸及到沒寫什麼的狀態下究竟寫出了什麼的小說奧義。孫得欽的畢業作品是小說集《離心》,收錄4篇小說,「我記得第一篇是亞當、夏娃和老人的神話故事,第二篇是類似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荒謬劇劇本,寫現代家庭一對夫妻的對話,我喜歡那種對話的方式,第三篇是故事夾故事的結構,第四篇則是設法把前三篇都收整起來,結尾帶到第一篇的人物,整體風格也許可以說是像是村上春樹的奇幻小故事拼盤吧。」
對於《離心》的完成,孫得欽獨斷地講:「我想我不是寫小說的料。」
▉走過對黑暗無比迷戀與耽溺的第一時期
為什麼喜歡文學?孫得欽如是作解:「因為感覺其中有著真理或真相可以指引我,我相信這是文學的本質,也成為我最大的動力。我好像一直在找某個純粹的東西。」所以他喜歡顧城,「早期嗜讀顧城,他的詩會有令人震驚的感覺,他純真得不可置信,但同時又是撕裂且痛苦的。那個階段還可以列出許多對我造成影響的作家,比如駱以軍、芥川龍之介、太宰治等,大致來說有迷戀、耽溺於黑暗的傾向。」
《有些影子怕黑》收錄的作品,有一半左右是大學時期寫完的,另外書中以馬賽克黑頁呈現的詩作,如〈戴面具的人們〉、〈青春期〉到〈初夏〉等,則在出書前的短時間內寫出。
第一本詩集出版的前後也恰好是孫得欽轉變期的到來,這本書也就有了在結束他上一個階段的意義。孫得欽慎重地解釋:「在我自己的區分裡,那是兩個時期的分水嶺。而主要讓我覺得事情不對,不應該是這樣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文學家通常不快樂,當然也有不自傷的文學家,例如楊牧,不過有一大部分人都在走向痛苦自毀。其二,如果文學是救贖是力量,沒有道理越寫人生越糟吧。」
再加上那些時日的孫得欽充滿大困惑,覺得活著很不自由不舒服,痛苦如影隨形。而在意識到文學似乎無法指向生命解答後,孫得欽開始轉向,「顧城的詩現在讀仍非常驚人,但我很清楚他不會是引領我的人。某個角度來說顧城挺孩子氣,他的撕裂是源於他的理想世界跟現實世界並不一致——可是啊,世界本來就沒有責任要跟你想像的一樣吧?」
孫得欽自覺必須推離黑暗的傾向,瞭解這種著迷不是答案,並且認清文學無法使用於他解除自身的痛苦與生命問題。同時他有種素樸直截的想法:「真理應當不是複雜的,它不該只有能夠理解各種複雜性的知識份子獨享。」無怪乎他會在詩作〈是有神祕〉寫下:「但不要神祕化//任何事情//才看得到最後那個神祕//真正的神祕//直直白白//陽光普照」。
「文學確實帶領我出發了,走上一個絕無僅有的道路。但如果我已經該前往下一個階段,可是文學沒有辦法跟我一起前往,怎麼辦?文學原來就只是要讓我通向對找尋生命迷惑的解答,沒理由非帶著文學持續邁進不可,不然,你反而是浪費了文學。我逐漸意識到,這裡必須有種斷然的放棄。」於是孫得欽有數年時光並未創作,直至這兩三年間,因為邀稿的緣故或某些契機,他才繼續重新寫詩,也可以說到了這個時間點,寫作的內在狀態差不多成熟了。
有趣的是他近來寫的詩,已遠遠超過《有些影子怕黑》創作的量好幾倍,「它正重新自然地生長,而我不刻意追求。以前好像都是在苦心經營,直到現在才真的有種詩跟我的生命脈動結合在一起的滋味。」
孫得欽露出一種充滿深度的笑容:「我一點一點的放棄,源自於文學的理解與累積的方式,然後又重新獲得。但也可能我放棄文學放棄得不夠徹底吧,道行太差,所以才有《白童夜歌》,也讓我懷疑自己可能是一個假裝還在寫詩的人。哈哈。」
孫得欽認為《白童夜歌》大致區分為兩類型,一種是直接到有時像是在說廢話的詩,另一種是很玄的詩。而對比於有著高度意象營造與技巧的《有些影子怕黑》,《白童夜歌》又直白又玄乎的裂解,就像是從打一整套中國式的長拳,忽然切換為直快的拳擊,一方面覺得突兀,另一方面又有種難以直言的悟性。孫得欽認為:「我感覺終於找到了自己的聲音,我喜歡用普通乃至庸俗的字詞。而與其說我的創作轉變了,還不如講是因為生命經歷了巨大的改變,創作只是反應這件事罷了。我後來讀書也不是在讀作品,而是讀到藏在後面的人以及他的世界觀。重要的是我內在生命如何發展,我有沒有看見那些不可思議的真實。」
▉第二時期,在詩歌中分享所見所體驗的另一個世界
放棄文學作為己身驅動力的孫得欽,後來的第二個時期,改朝向身心靈領域。他的原生家庭篤信佛教,母親會做早晚課,以致於孫得欽在小時候就皈依了,甚而有法名,當然那是他還什麼都不明白的時期,不過他確實一直對此一領域的探祕感到興趣。爸爸呢則是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的書迷,家中都是這位印度靈性導師、作家的書。孫得欽直到大學時期才從父親那兒借來克里希那穆提的書,此後也持續接觸同一領域,包含另一位大師奧修(Osho),「前者說話比較像知識分子,很嚴謹、很細緻,理解很困難,他思想純淨而且鋒利,認為追尋沒有方法,或者說是沒有道路的道路。而奧修則比較狂野,他什麼話題都談,有一百多種靜心方法,讓你去找尋那個生命更核心的解答。但我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讀懂什麼。」
真正的轉折點有兩位,一是艾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他最著名的書,名字叫《當下的力量》,孫得欽語氣平靜:「這才是真正的轉折點,他為我開了一道門縫,讓我目睹了真的有些東西在那裡,看見並抵達那裡是可能的。當下是什麼呢?其實,我們常聽到的活在當下根本是廢話,事實上根本沒有辦法不活在當下。意思是,你有任何辦法改變現在這一刻嗎?此時此刻你坐的姿勢、你的呼吸與聽到吃到的東西都是無從變異,你可以站起來,可以做任何努力,但那已經是下一刻,抵達了下一個現在。每一個當下都是不可改變的,所以,痛苦跟快樂的分界其實是你接受或不接受而已,你確實有這個選擇。而重點就是我是否認知到自己正在做這樣的選擇。」
再來是蔡神鑫《真我與我:印度靈性導師拉瑪那尊者的生平與教誨》所推介的印度上師拉瑪那.馬哈希(Ramana Maharshi),「我提到這些人,其實講的都一樣,就是『看見自己』。克里希那穆提說『認識你自己』,拉瑪那的核心也是一樣,只有三個字,『我是誰』。我是誰呢?我是我的身體、身分、思想嗎?都不是,唯獨去除所有你不是的,剩下來不會消失變動的才是你,合理吧?但那是什麼呢?我讀到的時候不懂,現在當然也不懂,但關鍵的差別是,現在問題本身慢慢在消溶了。」
在訪談過程中,孫得欽亦屢次強調會避免使用某些會指向特定範疇產生框限的字語,「因為它們在一般語境被濫用、淘空了,我想盡量避免讀到的人用標籤化的方式理解。所以我更喜歡普通的字,亦即沒有特定指向的字。像神跟愛就是普通的字,是廣泛的,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想像。對我來說,神是正發生的一切,也是關於『我』的錯誤信念悉數拿掉以後剩下來的東西。修行、靈性、當下、因果等詞彙就會自然被導向佛教,容易聯想到某些範圍。而且聽起來太崇高了,我一直喜歡定義自己是個庸俗的人。」某個面向來說,孫得欽更想要驅除黏附在這些詞語上的既定印象,因此他想到的解法是用詩歌語言去寫靈性追尋的內容。
孫得欽沒有開示者的高上姿態,比較是闡述再基本不過的生活事實:「信仰也是我會避免的字,因為聽起來好像是你要憑空相信一個很遙遠的東西,但其實那個東西是活生生的事實,就在眼前,可以直接看到的,看看周圍這世界,一片葉子也好,顯然有著極其龐大的什麼在作用著,看見這一點,自然會確知「我」渺小到不可思議的地步,而產生某種崇敬,在這個脈絡底下,信仰就是一種活著的品質。如果是這樣的定義,我就會使用這個字。」
孫得欽誠懇自白:「第一時期影響我創作的都是文學家或詩人,但這個領域的人容易自我戲劇化,陷入黑暗的深淵。在第二個時期,影響最大其實是靈性的東西,可以說我並沒有在追求詩,而是在嫁接、揉和這兩個領域,成為一個通道。」如同他在《白童夜歌》後記所寫:「白色的童子從廣袤的黑夜裡浮現……唱出另一個世界傳來的歌」。
孫得欽緩和地結語:「黑暗不是敵人,沒有理由要去對抗黑暗,事實上也打不贏,它本來就在我們的生命裡了,可以去接受它擁抱它但不必著迷它,看見它本來的樣子就好。從一切皆幻、都沒有意義的絕望盡頭,轉換到到一切都可以全部投入並發揮所有可能性,我本來以為「平靜」已經讓人很滿足了,但我最近才認識到,現在才剛剛抵達起點而已。寫作的人,好像有責任當一名引誘者,讓人看見那超乎想像的世界是可能的,也是存在的。我希望自己是一個中介、橋樑,分享我所見所體驗的,讓其他人也能看見,雖然那體驗的程度根本只是皮毛而已,但光是看見那一道門縫,就足以改變生命裡的一切。寫這本書其實有一個動力是,想提供一種心靈的健身器材,心靈的肌肉強壯起來,才能探索世界。生命廣闊到不可思議,不去探索所有可能性,太浪費了啊。這話也是對我自己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