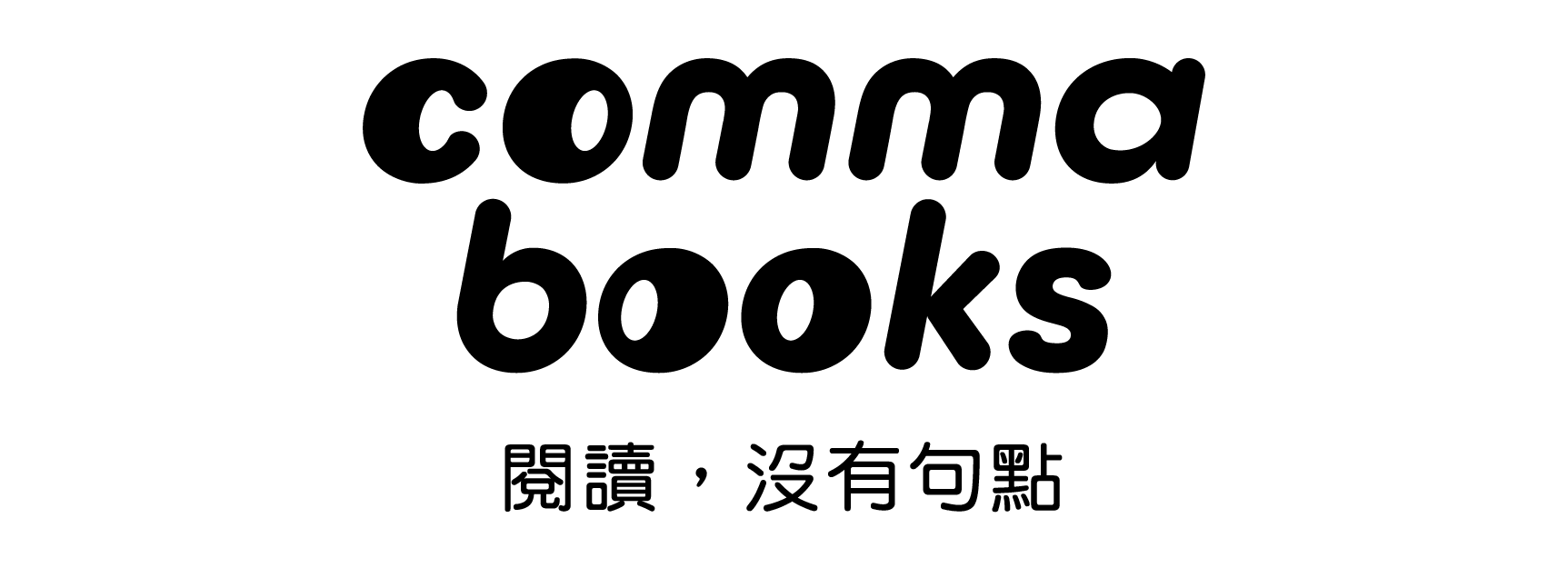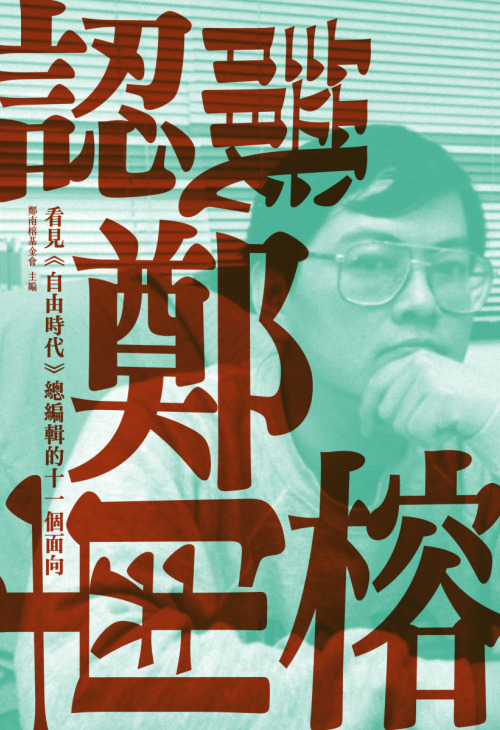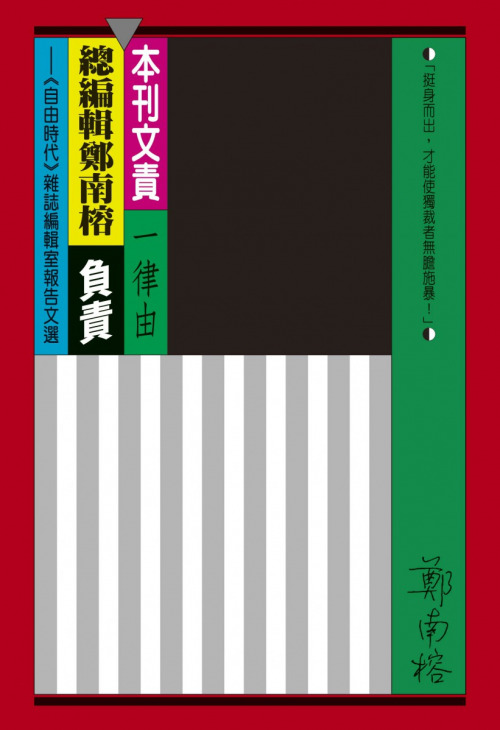忙忙忙!機智的出版人對抗警總,機智的讀者對抗Rage Bait!——鄭竹梅、朱家安談言論自由
在數位排版尚未問世的 1980 年代,辦一本對抗體制的黨外雜誌,除了持續鍛鍊發揮自身的採訪與出版專業,更需要用各種不同的「機智」手段才能在國民黨政府各種審查與滲透中保護員工、進而向全台灣讀者發聲。
「小時候,雜誌社就是我的遊樂場。」在臺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舉辦的「鄭南榕的機智雜誌社生活!——關於怎麼做雜誌、也關於百分百言論自由」講座中,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鄭竹梅指著一張黑白平面圖,帶領讀者穿越時光,回到那個充滿油墨味與菸味的《自由時代》週刊辦公室。

這場對談由鄭竹梅與哲學作家朱家安主講,兩人從「戒嚴時期」與「社群媒體時代」雙線出發,拆解一位總編輯如何爭取「百分百言論自由」,同時也探問當下每一個人:活在資訊戰之中,我們是否仍擁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不可以停下來!無論如何每週都要發刊!
 對現代人來說,辦雜誌是電腦前的工作,但對鄭南榕與《自由時代》雜誌社員工來說,光是採訪、寫稿只是基本,送印前整個空間都會變成滿是刀片與膠水的戰場。鄭竹梅回憶,當時的美術部門沒有 Photoshop,每一頁版面都是手工剪貼拼湊而成。
對現代人來說,辦雜誌是電腦前的工作,但對鄭南榕與《自由時代》雜誌社員工來說,光是採訪、寫稿只是基本,送印前整個空間都會變成滿是刀片與膠水的戰場。鄭竹梅回憶,當時的美術部門沒有 Photoshop,每一頁版面都是手工剪貼拼湊而成。
每週一次的送印日,辦公室每個人都在忙,總編輯辦公室內,鄭南榕一邊改稿,一邊思考下一步:要是這期雜誌出了,雜誌社就被禁怎麼辦?為了規避當時新聞局的頻繁查禁,鄭南榕展現了驚人的機智。他一口氣申請了二十四張出版事業登記證,今天《自由時代》被查禁了,下週就換個名字叫《先鋒時代》、《民主時代》,唯一不變的,是封面上那兩個紅色的「時代」大字,以及那股與體制周旋到底的韌性。
這種諜對諜的戲碼,在國民黨政府緊盯監視之下,自然延伸到了雜誌社的空間配置與物流。「為什麼雜誌社裡要有暗房?為什麼要自設打字組?」鄭竹梅解釋,這不是為了專業分工,而是為了防諜。「如果送到外面的照片沖印店或打字行,稿件很可能下一秒就會流到警備總部的手裡。」
雜誌印好後,運送更是一場游擊戰。「怎麼運出去?」主持人陳夏民補充了當時的細節:「他們把雜誌藏在菜車的高麗菜底下,甚至利用靈車、救護車來運送,因為警察通常不會攔查這些車輛。」
鄭竹梅也強調,如果沒有讀者與其他協力者同心齊力,《自由時代》週刊也無法觸及全台灣各個角落。「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要傳遞跟傳播,這些事也不是只有鄭南榕一個人做,中間會要有印刷廠,會要有發行商、通路商等單位。那個時代的臺灣人求知若渴,就是希望有主流媒體以外的訊息管道可以知道真相。」

為什麼一定要「百分之百」?
大家耳熟能詳的「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是鄭南榕的名言,但許多人或許會問:九十趴不行嗎?為什麼一定要百分之百?

鄭南榕曾在《獄中日記》寫道,當時美國的自由度是99%,日本是98%,而臺灣只有50%。對他來說,100%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烏托邦,而是一個必須死守的底線。哲學作家朱家安邀請大家思考:確實,現代所有民主國家都一定會禁止某些言論,你不能擅自發佈災難預報,也不能誹謗或詐欺,但在我們討論追求百分百的言論自由時,難道我們追求的是擅自發佈災難預報或詐欺的自由嗎?
言論自由的範圍涉及價值判斷,是民主社會的成員權衡出來的,而這權衡過程,當然也需要言論自由的支持,才有機會實現。
言論自由呈現的「群體生活價值」
 朱家安引用英國哲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分析言論自由能帶來許多重要好處,例如讓人們藉由開放的討論更接近真實,並且能接觸各種價值觀,找到自己認同的人生路線。在此觀點底下,長遠看來,言論自由不只是個人的自由,而是讓人們能夠從彼此得到幫助,一起走向更好的人生。
朱家安引用英國哲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分析言論自由能帶來許多重要好處,例如讓人們藉由開放的討論更接近真實,並且能接觸各種價值觀,找到自己認同的人生路線。在此觀點底下,長遠看來,言論自由不只是個人的自由,而是讓人們能夠從彼此得到幫助,一起走向更好的人生。
言論自由不但重要,而且特殊,朱家安解釋:當你擁有言論自由,因此能基於你的專業提供更好的資訊,那麼別人也能因此得到好處。在這種觀點下,言論自由也展現了群體生活的價值。
反過來說,這也能說明,當政府箝制言論自由,這帶來的代價也不只是你不能說話而已:「如果你活在一個不能說真話的社會,你失去的不只是談論政治的權利。你失去的是與他人建立『真實關係』的能力。你不敢跟鄰居抱怨物價,不敢跟朋友討論時事,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誰會去告密。極權統治最可怕的,不是關押你的身體,而是剝奪了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朱家安這樣分析。
從警備總部到演算法Rage Bait
然而,四十年過去,警備總部解散,我們現在擁有鄭南榕夢寐以求的自由了嗎?講座下半場,焦點轉向了當代的數位困境。「過去,我們害怕的是『封鎖言論』,現在,我們面對的是『資訊戰』。」朱家安點出了當代最棘手的問題。
 在戒嚴時代,獨裁者用「減少言論總量」來控制思想;在社群時代,有心人士用「製造大量垃圾資訊」來淹沒真相。朱家安提到牛津字典的年度代表字 Rage Bait(憤怒誘餌),意指網路媒體故意挑起憤怒來賺取流量。「以前的公共討論無法讓大家接近真實,因為大家怕被抓,不敢說話;現在的公共討論難以讓大家接近真實,因為資訊戰和社群平台的氛圍對誇大、情緒性的資訊有利。雖然形式不同,但結果是一樣的:我們依然無法進行理性的公共討論,基於真實做出政治判斷。」
在戒嚴時代,獨裁者用「減少言論總量」來控制思想;在社群時代,有心人士用「製造大量垃圾資訊」來淹沒真相。朱家安提到牛津字典的年度代表字 Rage Bait(憤怒誘餌),意指網路媒體故意挑起憤怒來賺取流量。「以前的公共討論無法讓大家接近真實,因為大家怕被抓,不敢說話;現在的公共討論難以讓大家接近真實,因為資訊戰和社群平台的氛圍對誇大、情緒性的資訊有利。雖然形式不同,但結果是一樣的:我們依然無法進行理性的公共討論,基於真實做出政治判斷。」
鄭竹梅也引用了 IORG(臺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當前中共正利用「民主失敗論」等敘事,試圖摧毀臺灣人對民主制度的信心。朱家安總結:「這背後的邏輯,其實跟當年的警總是一樣的,那就是『不把你當人看』。過去的國民黨不認為你值得擁有民主社會公民的種種權利,所以禁止你發言;現在的共產黨不認為你身為民主社會公民的意見有什麼重要的,因此用假消息把你的意見覆蓋掉。」
只懂少少的議題也沒關係
面對資訊爆炸與認知作戰,現代讀者該如何自處?「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培養一種『知識上的美德』(epistemic virtue)。」朱家安建議。不管是我們身為民主社會公民的責任感,還是社群時代的環境,都引誘我們「每個議題都要懂點」,但這或許是錯誤的選擇。假設你很在意某個社會議題,你寧可哪種情況發生?
- 有兩千萬人,每人花五分鐘了解這議題,然後投票做決定。
- 有五千人,每人花三百小時了解這議題,然後投票做決定。
議題很多,人也很多,但如果我們每個人的注意力都一樣分散,就只會得到很淺的結果,無法發揮群體的力量。挑一個你在意的議題,刻意阻隔雜訊,深入去讀一本書、聽一場講座,不要一次在意一百個議題,結果只能在每個問題上沾沾醬油,而是好好思考自己能為某幾個議題持續奮鬥。朱家安認為,如此一來,不但議題的專家會增加,我們的生命也會更充實。
鄭竹梅則回應,這其實就是一種「腦部運動」。從戒嚴時期求知若渴的讀者,到現在資訊過載的網民,我們始終需要透過閱讀與思考,來鍛鍊自己的心智肌肉。「回看過去,都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