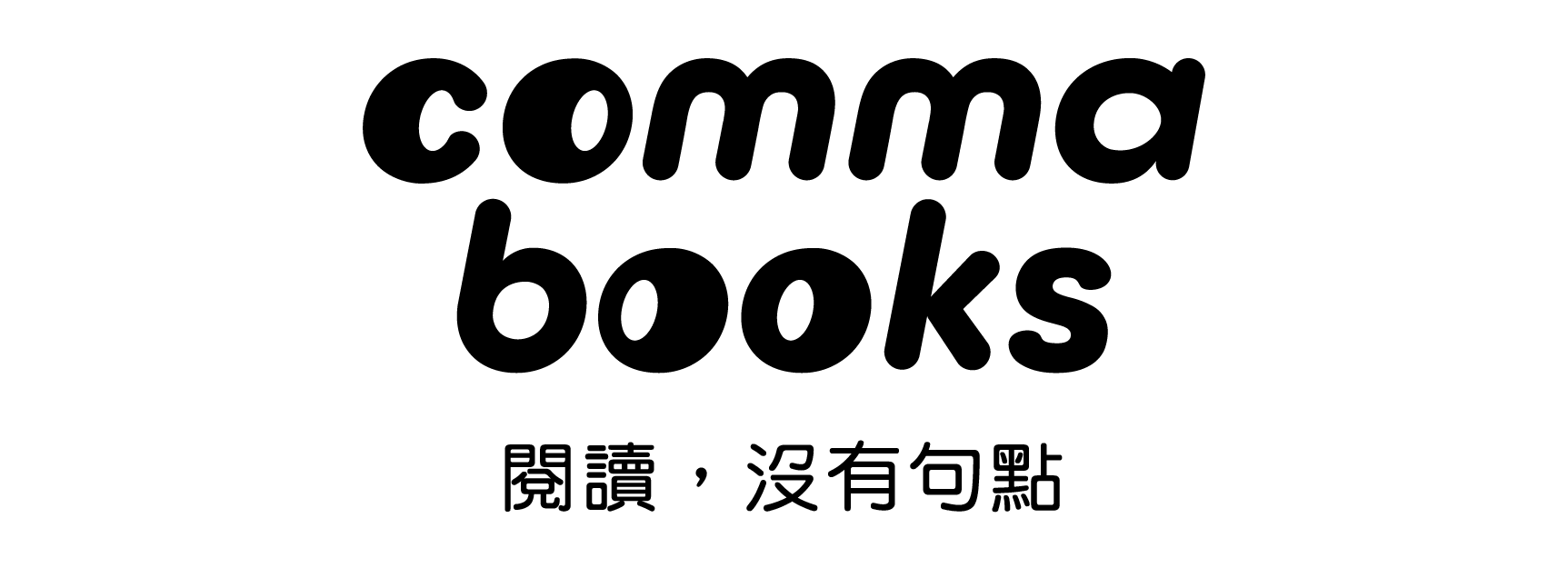閱讀》你不需要變成美麗的獨角獸——5分鐘讀完陳夏民散文〈我曾是爪哇人〉
我還記得,二零零七年剛從印尼回臺灣時,下午三四點,腦中就會下起泗水的午後雷陣雨,瞬間聚攏的厚重黑雲,沒多久便淹過輪胎的積水,關於印尼的回憶,彷彿經過數位修復的經典電影,在腦海重播時永遠那麼清晰。
因為印尼,我才相信每一塊土地都有其魔力,能讓生活在上頭的人慢慢染上同一個樣子。在印尼生活的後期,我已經不會被認為是外地人了。而剛回來臺灣時,也經常在火車上或桃園後站被印尼人搭訕聊天。工作認識的朋友甚至以為我是印尼僑生。
是啊,Aku wong jowo(我是爪哇人),這是T教我說的爪哇話,他說我在他眼中是一名很典型的爪哇人。我不曾問他為什麼,就自然而然接受了。
要融入異鄉生活,其實不太容易。
在印尼入睡的第一個夜晚,我在清晨驚醒,窗外擴音喇叭大聲放送號角與奇異的吟唱,以為是發生戰爭了,昏暗之中驚坐起身,嚇出一身冷汗。隔天才知道那是清真寺的祈禱通知,過了不久也就習慣了,只要一躺上床就陷入極深沉的睡眠,幾乎不曾聽見那聲響。
平日,我在教室裡教孩子們中文與英文,而在生活場景中,跟著學校孩子們的節奏,向同事與任何願意開口與我對話的人,學習簡單的印尼語。kata kata,一個字一個字地記憶,試圖以他人的母語和世界溝通。還記得令人痛苦的b和p發音總是讓我頭痛,把陰毛(jembut)的b記成p;那時每一次吃飯點餐都像在玩真心話大冒險,直到終於可以自在從容地看懂菜單,用手吃烤魚,或是在路邊攤喝一杯即溶咖啡配炸物當作下午茶。好幾次,我都覺得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家,那是過往在桃園或是花蓮所不曾有過的感受(儘管一直以為終究要在花蓮養老,因為他們都說花蓮的土壤特別黏)。
其實,印尼的生活並不特別舒適。那炙熱的太陽曬得人頭昏,午後打雷下雨路面就會淹水大塞車。為了融入環境,我每吃一塊炸豆腐都和當地人一樣,搭配一小根生綠辣椒一起吃,吃到後來覺得胸口有灼傷之感(我猜想是俗稱火燒心的胃食道逆流)才喊停。而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每到一處新地方定居,一定要生過一場大病才算是真的融入,這件事也的確發生了。
某個週末,我與同事們前往泗水近郊的野生動物園參觀,看著各式各樣的動物穿梭林間,甚至有長頸鹿舔舐我們的擋風玻璃,惹來車內乘客諸多尖叫。我還記得那天陰鬱不已,空氣中積著濕氣,雨水零星幾滴始終下不來。車內冷氣很強,上下車的時候,能夠明顯感受皮膚上貼著一層濕冷水氣,空氣中蔓延著奇異的反差。不舒服。我拿著數位相機,記錄著當天的一切,然而,檢查照片時卻發現,小小的顯示螢幕上,每一張照片都有一大塊狀似墨漬的紫色壓在上頭。雖然我壓根認定是機器故障,但那奇形怪狀的紫,鬼影一般壓在照片中人的五官與肢體上,看來讓人心生不快。後來,我決定不拍了,全心投入其中,不去多想。
入夜之後,我全身發寒,開始盜汗、發高燒、上吐下瀉。有生以來,第一次有著瀕臨死亡之感。那一個禮拜的時間,幾乎忘了自己怎麼熬過去的。只記得前幾天吃了感冒藥,但完全無效,整天就是頭痛跑廁所。幸虧有好心的同事幫我按摩,helper看我一吃肉就吐,便幫我準備稀飯與素菜,才讓我撐了幾天。
終於,成藥也沒用了,同事們請總務處的一位華人老伯帶我去看醫生,他眼睛小小的,戴著一副眼鏡,始終微笑著。我還記得我們抵達了一間灰色的大醫院,我坐在長廊等待醫生叫號,但一切過於緩慢。看了醫生,老伯權充翻譯,但我完全不知道那病症是什麼,只記得醫生叫我喝寶礦力補充電解質,接下來,便是另一段侯孝賢式長鏡頭的等待領藥,長廊邊的白色窗簾在風中慢慢搖曳。
我猜,那是登革熱。那一個禮拜,瘦了五公斤,臉色蒼白到學生覺得我撞邪。也就在那一次大病之後,我完全適應了印尼的水土。
說也奇怪,就算遭遇了再怎麼奇怪或是不順利的事情,甚至是差點死在那裡,對那片土地的喜愛就是橫在眼前。也因此每當放假踏上故鄉土地,內心生不出相同的感情,我便覺得有些歉疚,也得坦承有些愛實在太不公平。
終究,還是回來了。
剛回臺灣時,每天都想回印尼。如今看來,這應該是一種「想回家的病」(注釋:引用自何景窗散文集書名):如果沒有一處更好的地方作為記憶支點,會無法支撐現實生活之重量。
想像中的故鄉益發美好,但距離引來了感情的質變,腦中的想望終究無法持久。在臺灣生活久了,那些kata kata便在追逐生計的過程中,一個字一個字地被忘記了。腦海中的畫面都還在,偶然在區間車上聽見印尼語也依舊可以聽懂一點,但我不一樣了。
某個秋天夜裡,我提早下班回到桃園,獨自在住家附近的公園散步。看著人群跑步、廟埕前面有太太們跳著韓國少女團體的舞蹈,領悟自己也可以和他們一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在現實的世界找到地方落腳,而不用一直回望充滿回憶的異鄉感嘆自己的格格不入。在臺灣,我以爪哇人自居。在印尼,我或許不自覺期待他們發現我是(很會說印尼語的)臺灣人。有一點點像是往復兩地的蝙蝠,期待著可以在獸界與鳥界都被接受,卻同時劃出一種獨特的結界,讓自己不屬於任何一邊。
這種領悟讓人感傷,因為這等於變相承認自己少了「特別的」稜角——如同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劇作《玻璃動物園》(The Glass Menagerie)當中,女主角細心呵護的、獨一無二的玻璃獨角獸。只是在我的劇本裡,當那一隻獨角獸的角被摔碎,我已經可以接受了。
我已經可以接受我與他人其實沒有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