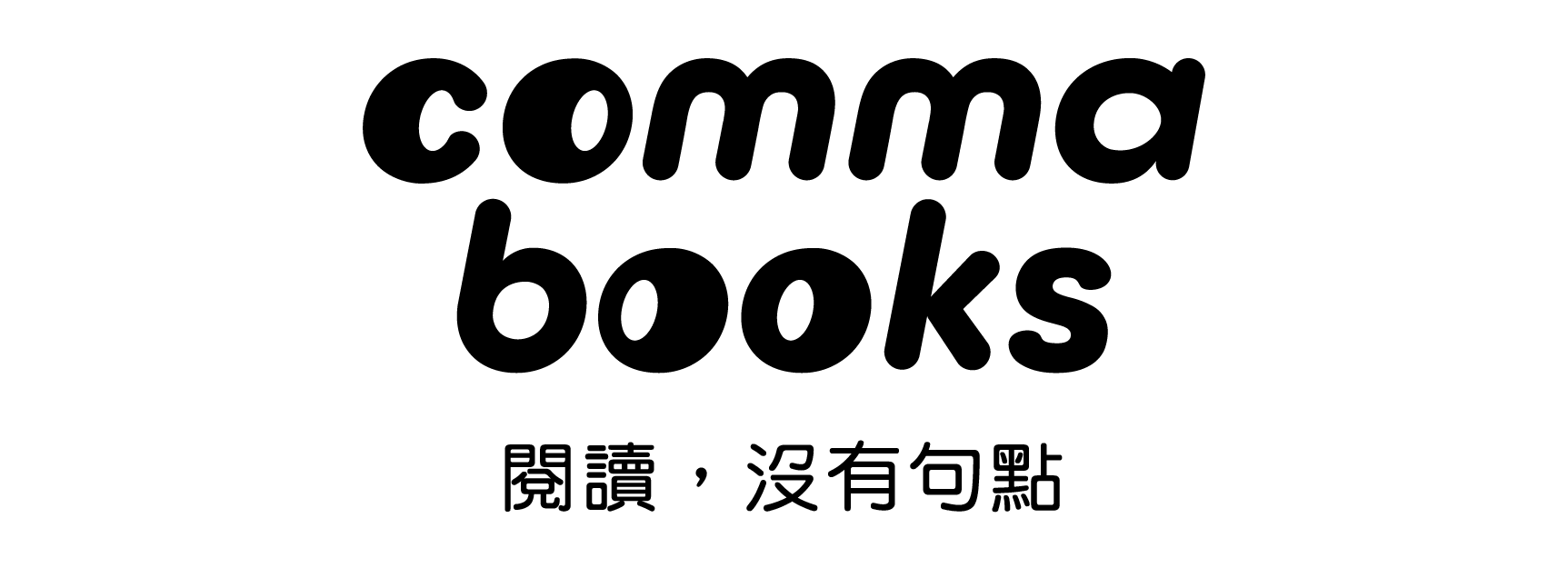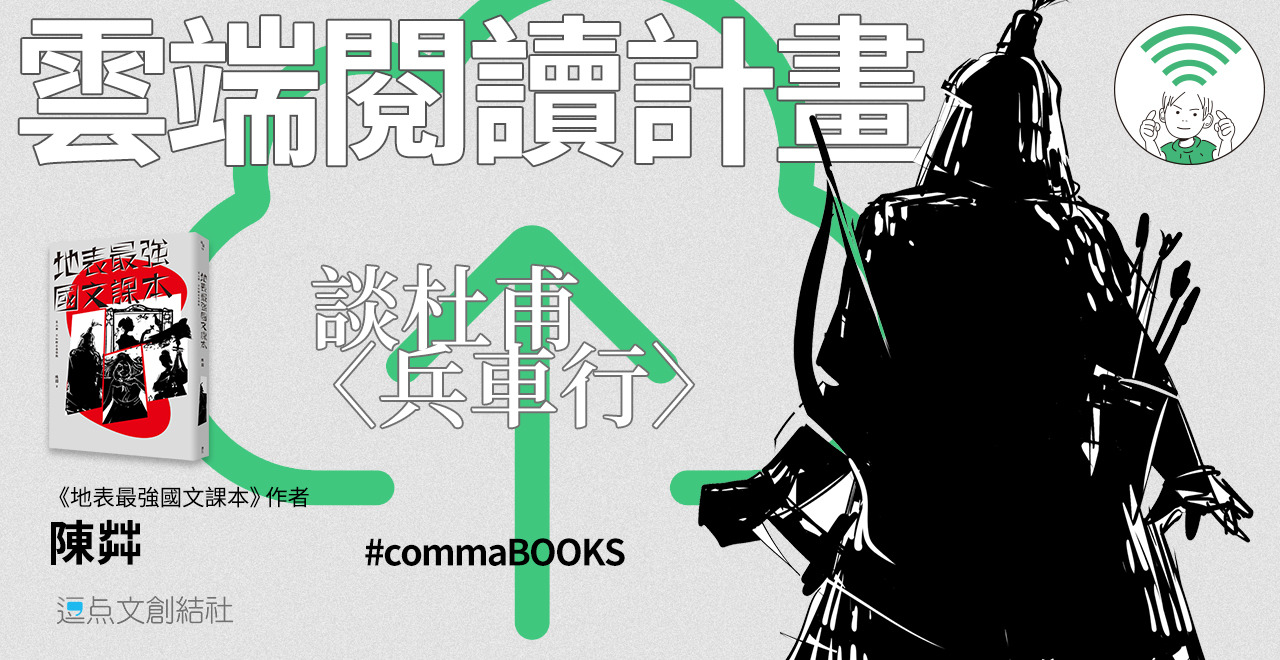
閱讀》哭聲直上干雲霄!七分鐘讀完陳茻賞析杜甫〈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
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賞析
哭聲直上干雲霄
一開篇,作者給我們的是一幅巨大而慘烈的人間離別圖。道上車馬喧囂,行人腰上懸掛著弓箭,為了帝國對少數民族的戰爭被徵召,爹娘妻兒在塵埃漫天的咸陽橋邊,拉著就要遠行的征夫,哭聲震天。
咸陽橋是古長安城通往西北的必經之路,這次徵兵,據考證應為唐帝國爭南詔一役。不過〈兵車行〉描述的本就不只是一場戰役—戰禍帶給人民的苦難都是一樣的。唐帝國在天寶中後期對外族用兵不斷,天寶十年出兵南詔,根據史書記載,這場戰役先勝後敗,損失的士卒太多,楊國忠隻手遮天,只向上報捷,又下令至民間捕人來補充兵員。這次的徵召很殘酷,士卒幾乎都是被強抓去的,《資治通鑑》就形容:「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這樣的記載與杜甫在詩中描寫的景況全然相同。
杜甫的詩一向被認為有歷史價值,他紀錄的都是歷史上確實發生的事,關於這場大徵兵,〈兵車行〉也赤裸呈現了當時的景況。只不過,這首詩作為杜甫社會寫實之開端,諸如「塵埃不見咸陽橋」、「哭聲直上干雲霄」等誇飾現實之景,畢竟難免詩歌語言之渲染。
這一類富有畫面張力的句子,很容易讓人聯想起盛唐的邊塞詩。七言歌行體在盛唐本就流行,由於句子的空間比五言詩多,韻律感也較強,多出來的空間讓詩人可以用更生動、誇張的描述,賦予詩歌更豐富的氣象,增強詩歌的氣勢。這個優勢很適合開展邊塞詩的畫面與格局,如岑參的「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澹萬里凝」;高適的「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鬥兵稀」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盛唐的邊塞詩雖然也寫戰爭,但多數時候詩人的心態較樂觀積極,對於建功立業有一番理想。有些作品雖也會提及戰事帶來的疾苦,但視角仍以邊塞為主,多寫戰場刻苦或征人艱辛。
〈兵車行〉是杜甫第一首社會時事詩,不只在杜甫個人的創作史上有特殊之處,在盛唐詩過渡到中唐詩的文學史意義上也有重要的標誌性。而杜甫以歌行體的流動感,以七言詩獨特的韻律,描寫了戰爭帶來的種種苦難,更為這類詩歌的題材開拓了新的版圖與視野,對於中唐的新樂府運動以及後代詩人的創作,都有不小的影響。
〈兵車行〉雖然不是邊塞詩,但很難說杜甫沒有受到這類盛唐詩風的影響。除了前面提到的幾句,後面的「邊亭流血成海水」等,更直接以想像力誇張渲染了幾場戰役的慘況。
相較之下,杜甫在經歷安史之亂之後,幾首真正被世人視為「成熟」的社會寫實詩,這類誇張的形容就少了許多。如〈石壕吏〉寫杜甫投宿石壕村,聽聞官吏夜裡捉人赴前線之場景:「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詩中沒有多少主觀描述,卻將戰亂中窮苦人家的悲慘故事寫得更為深刻透徹。
又如〈垂老別〉,寫戰爭殘酷,連步履艱難的老翁也不得倖免。「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人生暮年依然被徵召,只能與老妻訣別,讀來特別沉痛。
這幾首詩是杜甫登峰造極的社會寫實詩,平實而深刻的筆觸,將一齣齣人間悲劇寫得淋漓盡致。相比之下,〈兵車行〉呈現的畫面張力雖強,但力道卻不比後期詩作來得深沉。
是以,嚴格來說,〈兵車行〉還不算完全成熟的「社會寫實詩」。而那些被人稱頌的社會寫實作品,也只能奠基於社會的苦難之上,奠基於作者不幸的際遇之上。當一幕幕慘劇在眼前搬演時,現實的荒謬成了文學作品最血淋淋的力量泉源,誇張渲染的文學手法反而多餘了。
道傍過者問行人
〈兵車行〉雖然是歌行體,但結構明確,這點前人也談過。仇兆鱉在《杜詩詳注》提及,這首詩是「一頭兩腳體」,全詩可分三部分:首句至「哭聲直上干雲霄」為「頭」,後分兩段,由「道傍過者問行人」至「被驅不異犬與雞」為第一段,其後為第二段,是為「一頭兩腳」。 這個結構自然是後人分析的結果,在杜甫那個時代,自然沒有什麼「一頭兩腳體」的概念。但至少就作品來看,杜甫在結構安排上也許有所用心。
全詩分為三段,結構很明確,首段開啟畫面,次段則以「道傍過者問行人」,讓詩歌轉入另一個階段。身為作者的杜甫,也許就是那位「道傍過者」,又或者作者只是聽聞路旁行人的對話,而此句以後則是「行人」的自白。
在這樣的情境中,無論是作者還是行人,都只是無關國家大局的小人物。在詩中讓小人物自陳生命經驗與社會觀察並非杜甫首創,實是古老樂府詩的習慣之一。前面提過,樂府最初源自漢代的民歌,反映了許多社會現實。這類作品經常出現底層人物的對話或自白,這樣的敘事口吻很能夠反映來自民間真實的苦痛心聲。
杜甫以一句「道傍過者問行人」,將前面的場景敘述,轉換成一個小人物的故事。而這個故事背後揭露的,就是「徵兵」在民間最直接的影響。
「點行」指的是官府點名徵召兵丁,「頻」指頻仍。行人解釋道:眼前會上演這場妻離子散、哭聲震野的人倫悲劇,全是官方徵兵的結果。「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意思是有人十五歲時就被徵調至北方,從事防禦工事。前面有提過天寶中後期玄宗對外用兵頻仍,這裡的「北防河」應該就是用以防禦吐蕃的工事。「西營田」是軍隊屯墾的田畝,用以提供打仗所需之糧食,若無戰事,兵士就需屯田耕作,這也是防禦吐蕃的軍事部署之一。
這人自十五歲就被徵調到前線服役,直至四十歲仍於邊界部署防禦工程,歲月也一去不返。「去時里正與裹頭」指的是當時年少,地方的「里正」(唐時負責管理戶口的地方職位)還替他束髮。十五歲在古代只是剛需要束髮的年紀,少年自然對此還不甚熟悉,「里正與裹頭」寫的正是當年年輕稚嫩的模樣。下一句「歸來頭白還戍邊」意思是當歸來的時候,頭髮已白了,卻又要被徵召去戍守邊境。這兩句話很巧妙地以頭髮串聯起昔與今,句子很自然,對比起來卻很沉痛。看似平凡無奇的句子裡,往往有細膩而緊密的關聯,這是杜甫擅長的寫作方式,後期的社會寫實詩更是爐火純青。
前面「或從十五北防河」的「或」字,是「有人」、「有些人」的意思,也正因為有這個「或」字,讓這些人生階段的具體經驗,成了普遍發生的事實。十五或四十,都只是大概的數字。這段日子裡,在年少時就被國家徵召的人民不計其數,也正因為這樣的事頻頻發生,作者才能夠直接針對個體具體描寫。年少離家、歸時頭白的征人,是那時候的常態,是一天到晚都在發生的人生故事。「頭白還戍邊」如此悲慘命運,杜甫也只幾筆淡淡帶過,這一切寫來愈是輕描淡寫,想來就愈殘酷。
而這一切由一個行人,一個沒有名姓的、極其平凡的人道出,正是樂府最原初的精神。歷史的聚光燈,也只有此刻才會真正照在毫不起眼的人身上。他們身上沒有光芒,卻是歷史本身,是統治者、掌權者談笑間就可能毀去的、微不足道的生命。
武皇開邊意未已
這首詩批判當時政權最直接之處,在「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兩句。邊疆的戰士已不知死了幾萬人,流血成海,但統治者依然野心勃勃地發動對外戰爭。
杜甫自然是反戰的,因為戰爭讓人民流離失所,使得生靈塗炭。前面也提過,人民是杜甫最核心的關懷,這一切都是環環相扣的。
杜甫的忠君思想很深,種種思維可說是傳統知識分子受限於道德框架的典型,許多人批判過他的愚忠,多少有其道理。
這裡開啟了一個較為複雜的問題。「武皇開邊」的決策,類似今日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姿態,自周以來,古中國社會一直存在著華夷之防,也一直賤視著這些「夷狄」、「外族」,國家對外用兵,有其道德與政治上的正確性。
在傳統文人看來,要從根本價值上去反對國家「擴張版圖」、「安頓外族」,難度非常高。不只是迫於國家威權,更是因為這些行為本身帶有自古以來的合理性,對外族用兵,是某種程度的開化,許多文人甚至醉心於此。前面提及的邊塞詩,有不少歌頌國家戰功的,用兵的對象清一色是非我族類的外族。
如果說杜甫此時已有反戰思想,那他如何安頓這些傳統價值的框架?以今日的反戰姿態來反對上位者對外用兵的決策,在那個時代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忠君愛國背後本就包含了對國家的認同,儘管知識分子也清楚有比這些價值更核心的精神,但他們基於對政權的認同,多數不會直接反對國家對外用兵,更遑論進一步的反思。
這與安史之亂後的刺激不同。安史之亂長達十餘年,唐帝國已飽受戰亂之苦,身歷一切苦難,要主動反思這一切並不難。然而,天寶年間的邊境戰事,檯面上仍處處被遮掩,許多「戰功」依然受到表揚。在這樣的氛圍之中,因著親眼所見的民間疾苦跳出來抨擊,甚至由此聯想到一連串的窮兵黷武帶來的民生凋敝,這就不容易了。
寫完〈兵車行〉之後,杜甫又接著寫了〈前出塞〉九首,可看作是〈兵車行〉的開展,其中有幾句話,或多或少能夠回答上面提到的問題: 「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意思是說,邊疆戰事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該過於頻仍。重點是在防禦外族入侵,如果能夠有效阻止也就夠了,又何必多所殺傷?
這段話雖有反戰的成分,但也可看出杜甫仍必須給予對外戰爭最基本的認同。無可否認的,這些意見十分消極,只能默默點出某些戰事實沒有發動的必要。杜甫對於掌權者的控訴一直都不直接,他只能不斷寫著民間的慘況,以赤裸的事實發出無言的抗議。
這是詩人的軟弱,但文學作品被擺放在無奈、無助的位置,往往又更為有力,想來確實諷刺。
生男埋沒隨百草
第二段寫征人被時局毀去一生,到了頭髮斑白仍在為政府奔波,想來直至老死也不得一日安穩。由這樣的遭遇,剝洋蔥般一層一層揭開帝國承平之治的外衣,看見早已千瘡百孔的社會面貌。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連年的戰爭,已讓帝國最基礎的產業出現大問題。民間男丁都被徵召去打仗了,山東二百州田園荒蕪,長滿了野草荊棘。「縱有健婦把鋤犁」,道出了民間男丁短缺的情況。戰爭直接衝擊了民間的農業,也就是直接衝擊了國家的根本,顯見此時的唐帝國早已問題重重。
民間人口男女比例的失衡與否,絕對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時代治亂的標準。當戰爭連年發生,男丁都被徵調,產業勢必動搖。
古老的樂府詩裡,早已提及這樣的現象,據記載,秦代民歌就有「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住」的句子,建安時代的陳琳寫〈飲馬長城窟行〉,就化用了這段,寫成:
「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
意思是,如果生下男孩子,千萬不要養大成人;若是生下女子則要餵以乾肉,好好照顧。只因為長城下方,戰死的軍士骸骨相堆疊,甚至無人能收屍。這一切無疑是人間煉獄最赤裸的寫照,而杜甫也承襲了這樣的書寫方式,寫下「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這些明顯前有所承的句子,意味著有些事一再重演,竟千年不易。
新鬼煩冤舊鬼哭
一再重演的悲劇,在杜甫的筆下成了最後的控訴。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自古以來,戰場戰死的從來沒有什麼英雄,只有一個一個無辜的冤魂。回顧全詩,也不必爭論寫的到底是哪一場戰爭,杜甫的筆下從來都只是民間的苦難,是軟弱的怒吼。
因為戰亂而徵調男丁,致使田園荒蕪;因為戰亂需要增加賦稅,但人民根本無力繳納。
古代的樂府,直接書寫當時的社會,被稱為是「緣事而發」,很多樂府更直接以內容為題,今日只需看標題就略知一二。
這些寫時事之樂府,到了建安時期,在文人手上又有了新的變化。他們開始使用樂府舊題,內容仍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如前面提到陳琳所作〈飲馬長城窟行〉,就是典型的例子。
杜甫的時代已開始自創新題,像〈兵車行〉這樣的題目,在古代並沒有出現過。這些樂府歌行,雖然沒有沿用舊題,但為了這些新發生的時事寫詩,又以詩歌內容為樂府的新詩題,比以樂府舊題改寫的新作,更貼近樂府最初的樣貌。
〈兵車行〉寫的僅僅是路旁的一段對話,簡短的詩句中,已將一個國家種種不堪的景況都說得很透徹了。最底層的人物所發出的聲音必然最不堪,卻通常不會被聽見。前面杜甫寫道「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意思是這些問題雖然被這位「長者」問起,但身為一個被徵調的役夫,又如何敢表達自己的憤恨?或者是,就算發出怒吼,卻又能改變什麼呢? 曾經有那麼幾個時代,人命如草芥,一切控訴又是如此無關統治者痛癢。杜甫自此詩後,踏上了成為一代「詩史」的道路,他的筆會愈來愈純粹,筆下的故事也愈來愈沉痛。
樂府精神之存在,賦予了詩歌積極的意義,同時也道出了歷史之無奈、人民之無助、詩人之無力。
詩人在這些從未停止過的苦難面前顯得軟弱,但我們卻也因著詩人的文字,看見每個時代黑暗的角落,看見個別生命的種種艱難。
杜甫有他的掙扎,也有他的天真,而他的筆最欲擁抱的,一直是這些人間最純粹、簡單的,所謂安穩日子,所謂生活,而竟不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