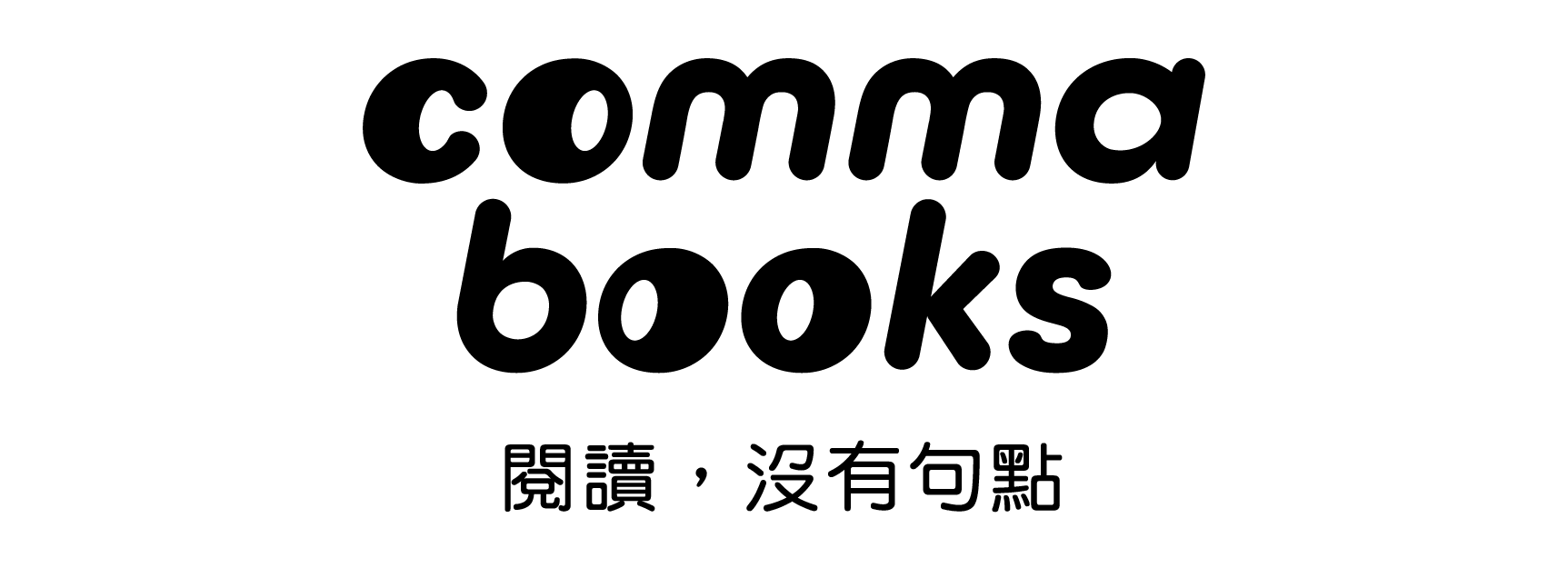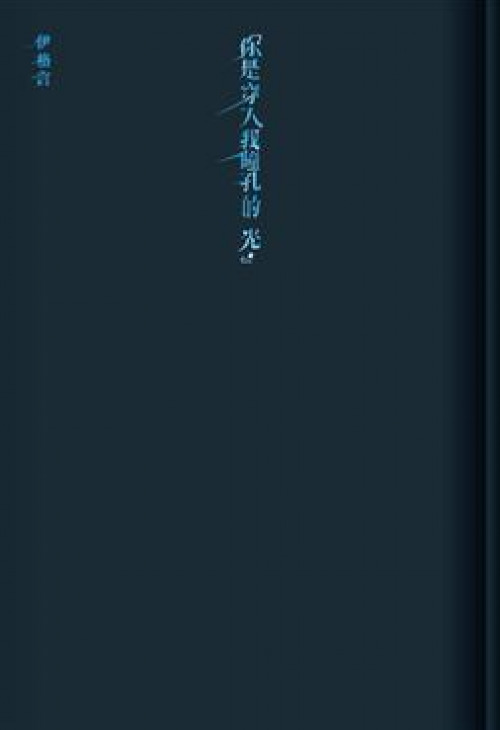閱讀》我終究還有可能理解,愛是怎麼一回事。七分鐘讀完伊格言散文〈萬中選一的幻覺〉
01. 願望
什麼是願望呢?偶爾遇到必須寫「寫作態度」或「得獎感言」或發表什麼明確文學意見的時候我容易感到困惑。我並非對那些文字的目的性或存在之價值感到困惑(有些人描述自己的「寫作態度」時描述得好極了,不過那不是我),我只是想到自己的願望。
每當有人需要我的「寫作態度」或「得獎感言」時我無法不想到自己的願望。天氣濕冷,我看見許多細碎的,漫步或躲藏於生活縫隙中的雪白光線。那光線如此零碎,像是來自細小的雨滴本身而非來自天幕或陽光。那些永恆的雨滴。走過人行道,隔著圍牆,校園裡伸展出來的樹木枝幹將自己的一部分投擲於潮溼的地面上。那些或大或小的枝幹或藤蔓。或陰影。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有種向它們——無論是枝幹或藤蔓——趨近的可能性。願望或大或小,生命本身又疼又慢。
我想遺棄它們。遺棄願望。或許就像我遺棄過去的自己。遺棄那個在晨光中醒來就會想立刻打電話給你的自己。反正你一定比我早起所以我不必怕吵到你。
但我好害怕吵到你。我好害怕。一切都像傷口,又疼又慢。
02. 百葉窗
夢中,百葉窗像是老電影一般篩過氣流,格柵或網狀的光線。我向來喜歡那種美麗的條紋,像我喜歡日落時分的室內那種總是帶著暗影痕跡的陽光。那或許已不是光線本身,而是光線的殘留,如同我們總錯覺光線依舊存在,但事實上光線只是「曾在」。「此曾在」。
許多時候我等待時間推移(「推移」可能會被察覺,當你發現格柵角度的偏轉,像一座空氣中的懸浮日晷;或者以聽覺的形式,當你將耳朵貼近時鐘,聽見齒輪細密齧咬進耳輪;甚或它可能不以知覺的形式出現,當你只是身處於那樣帶著暗影痕跡的光線裡,感覺自己就是那時光流逝的縫隙中無可迴避的暗影),在自己的幻覺中調整百葉窗的角度。在夢裡,讓自己決定篩過什麼、不篩過什麼,讓自己決定可以用百分之幾的心緒去想你,或迴避你。
迴避記憶。它們彷彿通過了意識的百葉窗,許多次之後,無可迴避地,在窗上積下的記憶的塵灰。
03. 畫廊
我在午夜時分抵達那家畫廊。鹵素燈打亮著牆上和空間中的展覽品。整座畫廊空盪清冷。巨大的,挑高廠房般的清水混凝土空間,牆上的攝影圖像予人以死亡之印象,而場地正中央的裝置藝術作品(作品說明上提到那是碳纖維與某種合金的混合物,介於灰與白之間,帶有藝術家不知以何種方式形塑的淡褐色污漬)則類似某種金屬織物,古生物化石般的結構骨骼。我感覺眼前的一切都呈現著比我的死亡更令人興奮、折服或嘆息的美麗。
但突然我又對這一切感到厭煩了。不,不是厭煩,是感傷,以及因過度感傷隨之而來的木然或無感(人極可能因為長時期經歷高強度的感傷而習慣或麻痺,局部性地)。如同在你面前,我將自己過去所有的欲望,野心,挫敗或對愛的信仰全數填裝在這巨大的空間中。它們於此被展示,在一個錯誤而又正確的時刻——午夜時分,城市靜謐,無雨,無塵,無光澤,除了我自身之外空無一人。
04. 異形
家具發出聲響。地板發出聲響。玻璃或窗發出聲響。晴日無風,天光隨著時間流逝而慢慢黯淡下去。這不是屋室該發出聲響的時刻。我想像它們因為光線之撞擊而遭受了空間本身的推擠。推擠如異形般侵入了這屋室之空白,屋室之身體。那音樂來自空間的嘆息。
而我的愛如同異形。我的情感,我的寂寞也如同異形。我如同異形。它們以我的意識作為宿主,長成了我全然無法控制的模樣。它們推擠自身,推擠著我,推擠著那意識與意識間神祕的間隙。彷彿深夜森林,無數記憶的碎片分布在黑暗中,占據著不明確的位置,吐納著無數微弱的鼻息,獸一般嗅聞著彼此的氣味。
我從夢裡醒來。感覺那些異形般的物事確實脫離了我,懸浮於我的身體之上。
一切都沉默了下來。它們輕輕吸吮著我的皮膚,輕盈的,靜電般的距離。
05. It doesn't make sense
米蘭‧昆德拉引用法蘭西斯‧培根:「人類現在明白了,人就是個意外,是個毫無意義的生命體,只能毫無理由地將這個遊戲玩到最後。」
如果我犯錯。如果我正經歷的終究只是自身生命的衰敗(在培根的畫裡,人的身體毫無理由,無理由至原本不應存在──像電視上那些親屬在波士頓馬拉松恐怖攻擊事件中意外喪生的人,那些未亡者的戰慄與眼淚:「It doesn't make sense.」那些亡者或傷殘者的鮮血與斷肢)。如果我的個人歷史終究只是偶然,一團隨機的聚合物。如果我負欠,並且可能在未來不確定的生命中負欠更多。如果我可以掏空我自己,或增生我自己;如同我終究不可能明白那些痛楚與愉悅來自何處。如果對我而言,真有「存在」這件事,如果我持續老去,老去至遺忘那我曾身處其間的「經驗世界」中絕大部分的形形色色——
我將不再與你說話。我將不再對這個世界說話。我將不做任何表達。我將保持沉默。我將不會向任何對象傾訴我心中那些細微的光亮(那星芒偶然存在,如同《大亨小傳》中那盞隔岸的綠燈,飛蛾喪生其中的火焰)。我將不會讓自己的形貌在任何欲望中扭曲,或表述這樣的扭曲。
It doesn't make sense.
06. 狼狽
最近不常見到牠們。偶然見到的一次,牠們顯然是來避雨的。
牠們是一對鳥。來的時候身上濕淋淋的,在我的窗臺。晨光照耀下,雨珠在牠們身上滯留,帶著溫潤的光芒。像珍珠。多數時候牠們保持沉默(儘管我知道冬天的時候牠們偷偷在我的熱水器底下築了一個巢——牠們覺得那裡比較溫暖?牠們喜歡加熱時那轟隆隆輕微的機器運轉聲?如果我是鳥,或許我會覺得那令我不那麼寂寞?偶爾我聽見咕咕咕的叫聲,不知道是不是牠們;儘管我也不知道那個小小的巢現在怎麼了),偶爾彼此對望。我靠近的時候牠們凝視我,黑色的眼珠帶著某種鳥類的靜定;但當我更靠近一些,牠們就飛走了。
但牠們現在被淋濕了。未曾抖落的發亮雨珠使她們看起來美麗而狼狽。我想起那段日子裡我也就是這麼狼狽;那或許是因為我曾對你說:我的願望就是每日醒來時能看見你就在我身邊。
07. 續稿未到
被編輯催稿的時候我很想搞笑地回應以「續稿未到,『萬中選一的幻覺』專欄暫停一次」。我真想這麼做,但終究明白那只能是個幻覺。而我們還擁有些什麼「不是幻覺」的實存之物?事實上很難。我的文字處理幻覺(誰叫我是個寫小說的?),我的生活填滿了妄想(比如妄想每天吃Häagen-Dazs而不會發胖),我的人際關係充滿了如履薄冰真幻不分的細微表情(我以為得罪了某甲其實沒有,我以為某乙喜歡我其實沒有),我的感情生活——呃,不提也罷。各種場合裡最常被讀者問到的問題總是「你的那些靈感是怎麼來的呢?」
我寧可把這樣的問題視為一種讚美——他的意思應該是,你的小說中充滿了瑰麗的奇想,神祕的場景,令人大驚失色的情節轉折,「你的那些靈感是怎麼來的呢?」——我說了一段我自己聽得很開心的話,而我想這大概也是幻覺。事實是,我敲鍵盤,喝水,燙青菜,刷臉書,每天都覺得自己沒靈感,而我的人生似乎永遠續稿未到。
08. 命運
「所以我可以信任你嗎?」她這樣問我。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我不是FBI的人,我也不隸屬於CIA。但事實是,我寫過一本間諜小說,我對世間任何實存或虛構的陰謀充滿了興趣。我懷疑國際金價暴跌與緊接著發生的波士頓馬拉松恐怖行動是有關聯的——儘管並不必然。我傾向於相信真有神或某種最高主宰的存在——儘管我們所處的世界可能只是祂的一場妄夢,一個無關緊要的奇想,祂手機裡玩到膩了不想玩的遊戲app(我們或許就像是那整排整排消失的糖果?)。昆德拉的名言: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 ——我一點也不相信這件事,我比較相信上帝大概連發笑的興致都沒有,否則我就可以跟祂玩交友軟體了(我很樂意逗祂笑的)。
「所以我可以信任你嗎?」當然可以,當然可以呀。上帝的陰謀(或陽謀,或「計畫」,或任何與其「意圖」有關的配套措施)都屬於我的興趣範疇之一——儘管我也不相信上帝有任何陰謀。我們的人生應該都被放在祂手機裡一個叫做「命運」的app(對,線上商店裡被分配在遊戲類)——但它最近好像沒開機。
09. 愛是可能的
我喜歡看你表演。你一人分飾兩角。
關於「變成另外一個人」,事情是這樣的:在那些你「變成另外一個人」的時刻,正常狀態下我們稱之為表演——然而文學上此一主題處理的往往是異常狀態(「表演」不在此一範疇內)——譬如《天才雷普利》(騙子),《紐約三部曲》(瘋子),《隱形怪物》(在愛情的烈焰之中形銷骨毀之人,騙子兼瘋子),甚或是我的《噬夢人》。問題是,真有「變成另一個人」這回事嗎?答案是可疑的,因為,少數時候,人原本並不真是「一個人」。人的人格其實並不穩定——所謂「人格」本質上是個植物模樣的活物,隨時存有歧出蔓生的枝椏;其內裡存在曲折的,不可見的紋路。是一個固定的外表造成了「人有一個固定人格」的幻覺。當然,於此處,個體彼此之間也有相當大的差異:人格大致穩定的人好相處,人格不穩定的人則不好相處。
我喜歡看你的兩個角色彼此鬥嘴。她們有愛,那愛是甜的;而且某些時刻我確知她們其實是一個人——那令我覺得親切,令我覺得,我終究還有可能理解,愛是怎麼一回事。愛是可能的。
——〈萬中選一的幻覺〉摘自伊格言詩集《與孤寂等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