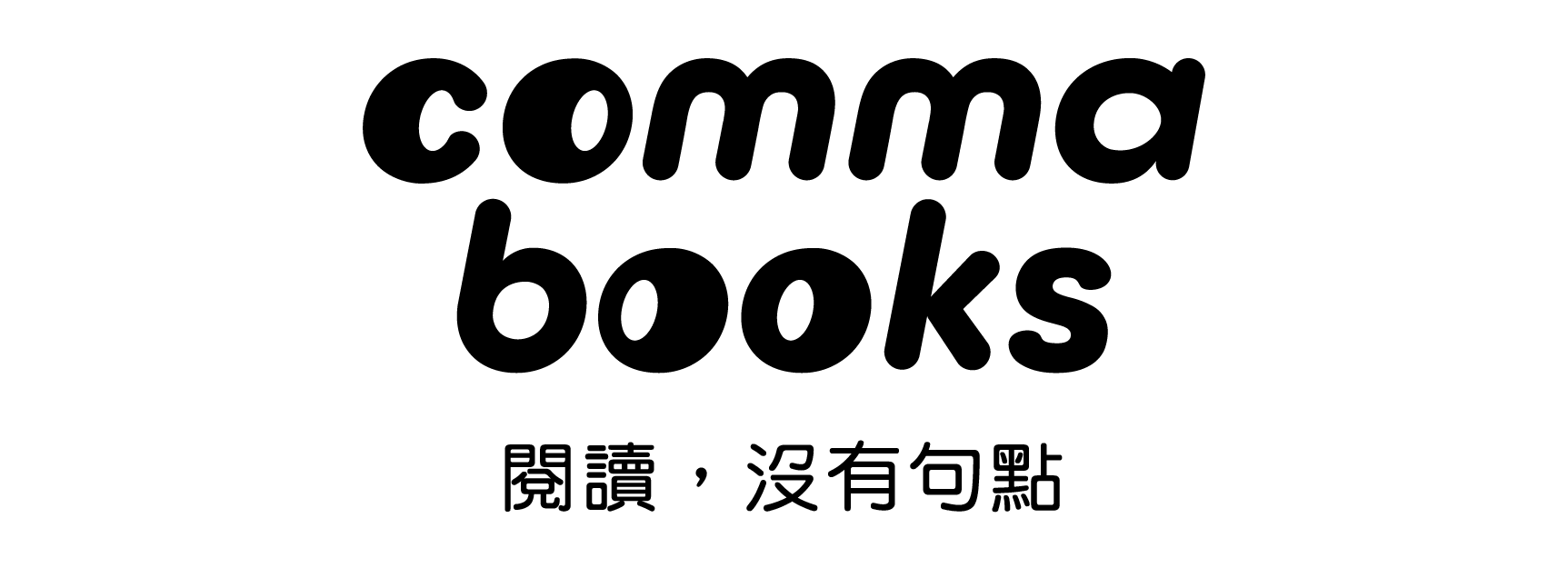遊樂萬劫不擋──閱讀James Thurber《想我苦哈哈的一生》
無所不在,也無孔不入的恐懼──讀完《想我苦哈哈的一生》,真正觸動我的並非James Thurber直視直述那些出人意表事件所激盪出來的荒唐好笑之味,反而是藏躲在整個時代普遍存在的陰影,關於戰亂、災難與形形色色的傷害之形影不離,跟隨人物一起移動的生死哀樂,不曾片刻遠離。人過著破碎殘敗的人生,人被己身的認知困住,以為深陷險境,書中那些繁花般盛開千繚萬亂五花八門的妄想情景裡頭潛伏著對現實的巨大畏懼。
無論是害怕盜賊吹進麻醉藥因而把家當堆在門口、神經兮兮以為自己睡著就會斷氣、夜半時分扔鞋以求驚嚇到訪夜賊、相信自己莫名被埋在礦井、試著從閣樓床塌陷殘骸裡拯救老公、在劇場表演時高喊世界即將滅亡、認定留聲機會爆炸還有電正漏進家中的每一個角落、只因為有個人跑了起來後頭便跟著跑起了一整個城鎮的幾千人還深信大壩潰堤洪水就在背後、想不起某城鎮的名字所以大抓狂非要挖醒熟睡的老爸聲色皆厲地要老爸背出所有城鎮乃在深夜時分搞得大家雞飛狗跳、所有人都咬且愛待在戶外於是只好自製一鐵片模擬雷電交加讓牠進屋免得搞死別人的惡犬、硬是把電動車當馬車一樣騎無法妥善控制因而暴跳不已、在兵役檢查被刷退但重複被調去檢查最後還莫名變成現場檢查役員的醫生,凡此種種,看到鬼影就開槍在本書裡獲得完美詮釋與印證。
讀著這些離奇的事件,我忍不住要想起Lawrence Block筆下瘋亂癲狂的睡不著覺的密探Evan Tanner經常在極極艱難的處境發動誇壯到當真神奇的行動(譬如阿富汗因為一台轎車被毀壞而掀起了街頭暴動)卻最後誤打誤撞總能堪稱滑翔地把事件與難題解決,又或者唐捐〈因為瘋的緣故〉:「閣樓上的轟女人/花出了她今天第103次尖叫/像軟軟、甜甜、黑黑的小刀,迴旋於我的耳道……仍然要起肖,要噴賽,要脫光光來跑跑/用長長長的污頭毛,裹住/罪惡的地球跑跑/而且鬼叫」,《想我苦哈哈的一生》真是不斷有人人都在鬼吼鬼叫的起肖場景,每一個磅礡的凶險都是誤會大了,遂令人不由捧腹大笑。
而角色的應對愈驚惶失措就愈可笑,同時我心中的哀傷也就愈濃烈。那些歇斯底里全都又可憐又好笑,非常眾生相的──我們不都有各自難以解離的畏懼之物嗎?有人怕高,有人怕蛇,有人怕鳳梨,有人怕草地,有人怕保特瓶等等,每個人都活在自身的恐怖顛倒,每個人都有著無法剔除在外的濃密暗影。而Thurber所處的當時與我們的當代又何嘗不是飽受不安全感的全面襲擊,日以繼夜地被各種危機炸裂。
看來輕快嬉戲的Thurber仍是明白的:「當然,逃不了的,即便康拉德筆下的吉姆爺也逃不了。那團特有的狼狽感就彷彿小狗一般如影隨形,任人搭什麼船、進入什麼蠻荒之地都甩不掉……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危機隨時都會一撲而來……」
而此書附錄小說更有意思,兩篇的關鍵字分別是慣用語與白日夢,前者是「若無其實、隨口脫出的句子,造就了我幼年時期魔幻一般的個人世界」,如有人說某個女孩「心都被她哭出來啦」,於是少年時Thurber便急忙忙把床都拆了也要找出被哭出來的心;後者則是活在幻想裡,在各種場景時刻,他都能夠順暢地進入白日夢狀態,展開多樣式冒險,成為高深莫測的英雄。
二附錄短篇披露了語言的極致想像力,以及對詩意時刻的召喚,體現著書寫者對生活與堅硬的時光的堂堂注視與優異輕盈的轉化力。對照本書正文,附錄小說其實仍是各種日常裡的脫逸不得之描摹。幻想無異於恐懼的延伸體(或者相反),而書寫和語言再現書寫者的昔日風景,並提供給讀者一份難能可貴、充滿細密心意的慰藉。
島國夢遊王駱以軍曾寫過:「……有時神祕經驗會突然降臨:眼前出現幻覺、金光、柔美的色彩,一種難以言喻的至福之感。手舞足蹈,心中澄澈透明。『如果在那時死去,我的臉上一定也掛著快樂的微笑。』」
我想,縱然身在地獄,Thurber的遊樂之心亦同樣這樣萬劫不擋吧。
(本文經沈眠授權,原發表於105年11月12日《更生日報:更生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