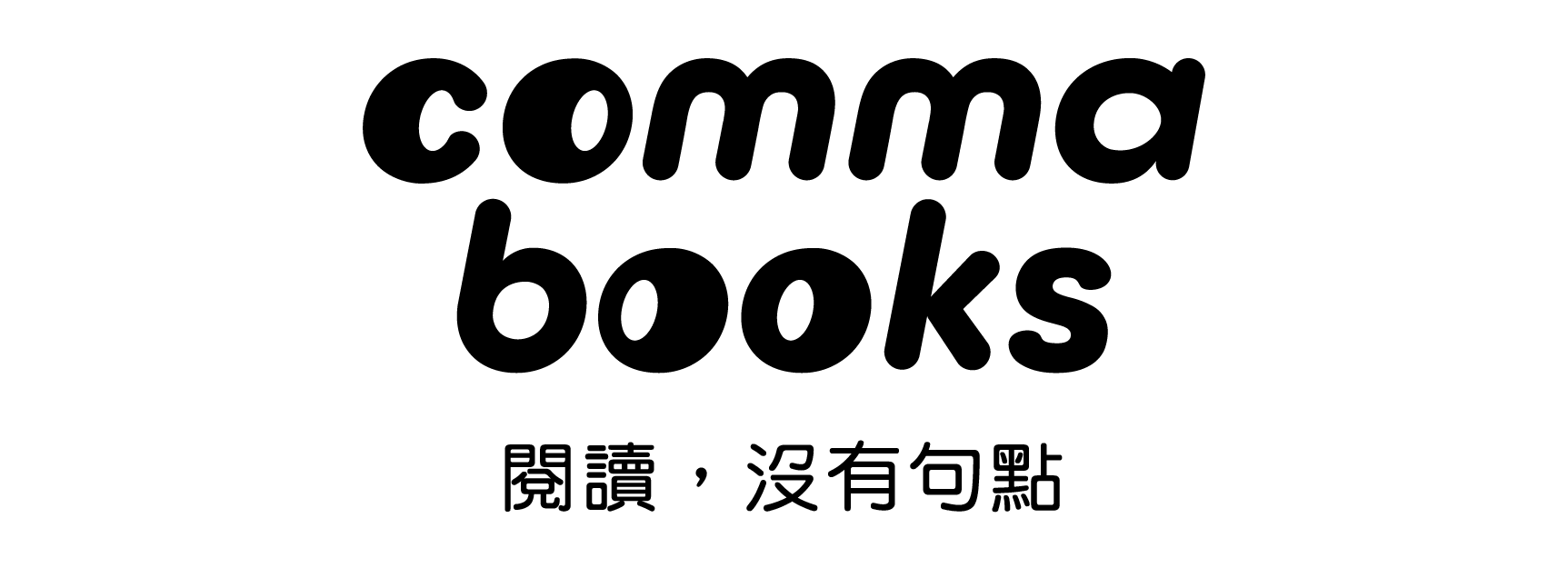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我已經死過了,只是僥倖回來。」——專訪《潔癖》林夢媧
1993年出生的林夢媧,屏東市人,大一時期開始寫詩。創作速度並不快的她,至今完成一本手作詩集《戀人狂》,並於2019年11月出版《潔癖》(獲第三屆周夢蝶詩獎、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補助、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藝文出版補助)。本次專訪規劃已久,攝影先行,拍攝當下,林夢媧身處尚未歇業前的有河Book;她一身金黃衣縷,表情空靈、氣質優雅,但眼神睥睨,隱隱帶著燃點,像是在等待爆炸。
 ▉從網路認識詩歌新世界
▉從網路認識詩歌新世界
「現代詩,不是課本上的世界,對我來說,」林夢媧語聲沉穩地說:「詩,一開始就是在網路上流竄的生命,像是莫名的動物,愈是看不懂,就愈是有奇怪的魅惑。」林夢媧最初便脫離紙本範疇進行閱讀,尤其是國中時期風行的Pchome新聞台更是她的養分,「那時比較紅的是無名小站,不過,我追看的都是Pchome,因為報台偏文藝,裡面的台長(創作者)寫的東西也都很怪,很特異。」例如曼陀羅或藏龍,前者甚至一篇發文下會有幾千則回應,更令她好奇。對林夢媧這個世代來說,網路是另一種荒野,充滿野生的力量,不被限制,無從規訓。
林夢媧談起對詩歌的興趣,「我所在的環境,離詩歌非常遙遠,周遭沒人可以理解,無論是家人或同儕,他們都覺得,創作這件事是奇怪且沒有意義。雖然無法被理解,但我還是堅持下來。也許是因為唯有繼續接觸,才可能遇到同類。」
但真要講到決定性影響,林夢媧笑說:「是九十九我魔。他每天都發文,有的是詩,有的是小說,也有影評、藝評,還有詩評,量非常多,範圍又雜。他的詩具有華麗到其實我一點都跟不上的文字,雖然看不懂核心,但就是覺得意象非常強烈,應該不是亂寫吧。」唯林夢媧也承認,她著迷的是他的現代小說和詩評。她會特地去誠品書局買他推薦的詩集,諸如嚴忠政《玫瑰的破綻》和鴻鴻《女孩馬力与壁拔少年》,「感覺一個璀璨得不可思議的世界正在打開,好像自己都變得鮮豔了。原來這是詩,」林夢媧驚嘆:「跟報台普遍在追求無意義的那些詩,完全不一樣。」
九十九我魔〈大宅男本紀〉寫主角去餐館,裡面有個黑箱子,寫一首詩丟進去,如果通過篩選,就可以跟來到店裡的女孩性交。林夢媧又困惑又好奇:「當時我很驚訝,怎麼會有人用這麼直接的態度寫性關係?幾乎是中性,」她停頓,想著更精準的詞語,「應該說不帶有色眼光吧,他就只是單純寫兩個身體,感覺得到人物心裡滿溢的寂寞,甚至是絕望。」
「我活在保守的、對女性自主並不尊重的環境,一直被教導性是可恥的,女生不應該理解自己的身體,更別說另一種性別。」九十九我魔卻揭破那樣的假象,林夢媧神情認真:「我開始明白,身體從來都是自己的。我可以有別的選擇,不必偽裝,做別人想像或期待的女性。我必須理解自己,學習整理情感,沒有人能教我。我得向內探索,成為真正的自己,而不是對外求解答。」至此,林夢媧世界觀徹底刷新。
2011年進入大學就讀,此時因為戀人的關係,林夢媧讀更多詩集,她笑著說:「他篩選過、覺得好的詩集才會買給我,比如夏宇、零雨、隱匿、辛波絲卡、吳俞萱、葉青、邱剛健、谷川俊太郎等。我是幸運的,因為沒讀過不好的詩集,所以基礎就比較好。」她開始想創作,寫完拿給戀人看,想聽聽評價。「他從頭到尾批評,包含用字不精準、詞語無意義堆疊,我真的大受打擊。」
講起磨練過程,林夢媧略顯激動,眼神帶煞,「當時的戀人,就是我現在的丈夫。這個人只要講到創作,就是百分百認真,沒有餘地。起初寫的詩,沒有一首他瞧得上,壓力大到不行啊。」她恨得牙癢癢,又覺得不能認輸,也不想放棄,堅持好幾個月,直到寫出〈我們得從現在開始〉,「他看完,一樣沒有表情,但說寫得好的時候,」林夢媧眼睛都是笑意,「有種被認證的感覺。」這首詩後來應隱匿的邀請,寫在淡水有河Book玻璃詩,是林夢媧首度公開發表的詩歌。「那像是完成一個世界觀,在有限的字數,做到最精確的表達。」林夢媧眼眉含笑:「現在我寫的詩,丈夫常會講我比他寫得更好。」
▉成為女性,創造自己的答案
「寫詩時,是在寫自己的血淚史,身為一名女性的血淚史。」林夢媧表情沉靜而語氣凝重地說:「女性活在現代,充滿各種痛苦,比如教育系統、社會價值,總告訴你要如何把自己的力量收起來,竭盡所能溫馴,不能釋放自身的特殊與能量。還有經常要面對男性把騷擾當作追求的行為,時時刻刻小心暗巷,那些潛伏的惡意與暴力。女人的神經質,有很大一部份是被環境養成的。」林夢媧總結:「女性的日常,習慣將自己藏起來,愈低調無聲,愈能遠離傷害。很多女人終其一生都致力於使自身透明化。」
林夢媧喜歡的詩人,性別剛好都是女性,零雨、夏宇、隱匿、吳俞萱、葉青等,當然也有少數是男性,如谷川俊太郎、邱剛健、王志元。「各有各喜歡的理由。隱匿是字句樸實,但裡面擁有深切的生命體會。夏宇示範每一本詩集是獨一無二的類別,而且像照片一樣,到處是令人有所觸動的畫面。吳俞萱過著獨特的生活方式,詩歌有野生感,見骨而蠻橫。零雨寫的日常,好像是神降,有天啟。王志元是說書人,正在對你傾訴,有故事性。谷川俊太郎詩裡的自然意象非常傑出。邱剛健是真誠的老男人,血淋淋寫詩。」
女性擅長與痛楚相處,包含月經、生產等不可轉移的經驗,乃至心智上的壓制,但也因此能擁抱更大的同理心、共感力,林夢媧輕聲道:「一般來講,女性的詩歌會讓我身在其中,好像就在那個痛苦的現場。但男性就會有距離。」談起偏愛女性詩人,林夢媧盡力說明:「女性的詩如同X光機,一切無所遁形。男性的詩就像全身鏡,得拉開來看,無法完全投入。」
林夢媧坦承,真正意識到自己成為女性,是作為母親開始,「從小到大,生理特質當然讓我知道自己是女性,但它並非穩固不變,至少心智內部,我覺得趨近中性。談戀愛時,也比較是靈魂撞擊靈魂,而不是愛上另一種性別。但懷孕時,從產檢到周遭人的對待,會明顯感覺到自己的物化。我被視為生產的器具。每個人都在對我下達指令,他們認定我是無知且無力的,我被迫小心翼翼地執行所有建議。」
那是煉獄般的時期,各種「不可以」與「必須」環繞在生活,「我強烈體會到絕對的孤獨,無論丈夫愛我如何之深,如何願意進入、理解一切,我還是一個人走在黑暗的森林,被那些以關愛為名的惡意圍困。」
隨後,經歷生產險境,「本來是要自然分娩,但過預產期一個星期多,仍舊沒有破水,所以排定催產,但孩子的頭顱位置不對,醫生緊急安排開刀,而且還是十字開法。但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戀人滿眼都是淚,而且對那個醫生充滿怒氣,上手術台我一直很擔心他。」回憶生死交關,語氣略顯緊張,「那是第一次意識到死亡,它不是靠近而已,它就在身體裡面。誇張點來說,我覺得已經死過了,只是僥倖回來。」
產後,又有另一番折磨,關於自我的喪失,「比如哺乳,所有人,包含醫護人員,都會擺出妳可以大方一點餵奶,好像我的存在價值只減縮到乳房,好像乳房有公共性,」林夢媧眼底爆亮,「但乳房是我的,是屬於我丈夫的,它甚至不是我女兒的,只是她短暫的糧食,其他人憑什麼看?我難道沒有拒絕被看的權利?難道我是母親,就不能有自己的私密?」日常遍布這般畸零的對待,「好像我不是自己,我不是人,我再也不是女人,只是媽媽。」林夢媧的聲音是溢滿的堅決:「因為這些將女性持續降低與剝奪權利的對待,我才變成女性主義者。」
林夢媧寫關於女性面對恐懼與痛楚的詩歌,但並不控訴激情,反倒有著溫柔的光澤,「也許詩歌是過濾器,寫詩時,那些雜質,不管是憤怒還是恨意都被清除,只留下最純淨的東西。」林夢媧淡淡地說:「那是自我潔淨的過程,最終也產生光滑與明亮的詩歌。裡面雖然有我的意志與情感,但寫出來後,就脫離我本身,是另外的存在,不再屬於我。」
產量不多的林夢媧對作品累積的速度,並不焦慮,「詩歌是生命無法解除的一部份。我感覺到它存在,在日常,在身體裡。但不是一定要寫。當然我一直被提醒要寫多一點,可是我不想把寫詩當作生意,我想要追求它作為一門技藝。寫詩是創造自己的答案。有時也會覺得心中有解答也就夠了。何況就算不寫出來,生活還是時刻有詩歌的顯影。」

▉《戀人狂》:愛情實現的器具與場所
「我和戀人一起發想並完成。結構是這樣子的,」林夢媧談起《戀人狂》,語氣輕盈,「我負責白情詩,他是黑情詩,各自寫34首詩,詩題都一樣,我的第一首是〈我們得從現在開始〉,最後一首〈戀人的時光〉,他則相反,詩集真正的最後一首,是我們合寫的〈我們作為戀人狂〉。」林夢媧自行列印與設計,請人縫合布製書封,完成手作詩集,「我們不打算出版,想要讓它是我們的愛情記錄。」
為什麼是《戀人狂》?林夢媧顧盼間是鮮豔的情緒,「因為我們都為對方癡狂。」她大笑。「我們算是比較誇張的一對。丈夫可以說有分離焦慮症,只要我一不在身邊,就會非常不安。我的個性算激烈,對戀人的獨占欲也很強,我要求他必須絕對誠實地對待我,所有發生過或剛剛發生的事情,我都必須知道。他走到哪裡都會主動報備。他全盤地接受我的統御,甚至自稱教徒。」林夢媧邊說邊笑,「我們分享一切,包括人生暗面,各自有多少任情侶,還有性經驗,難堪的醜事、軟弱與恐懼,無一遺漏。」
如此的緊密難道不怕失去隱私與自我空間嗎?林夢媧正色道:「隱私是為維護自身的孤獨,藏匿不想為人所知的祕密。但我跟戀人不需要保護機制,我們尊重孤獨,沒有誤會愛情會把兩個人變成一個人。相反的,我們清楚愛情就是兩個人孤獨的總和。我們學習、尋找更適合彼此的生活方式,每天認識彼此的變化。我們依然有隱私,只是隱私也是雙人份的。」
林夢媧與丈夫為彼此上癮,也成為對方的解藥,如若互相作為心理醫生,「我們每天對話,分享工作與創作,沒有厭膩,保持緊密聯繫,但也有自處的時間。」她言笑晏晏,「我們都是全心全意。他不會讓我有擠壓自己的感覺。他是個有陰性靈魂的人,願意瞭解女性的身心機制,不會獨斷,要我變成他的附庸。我寫詩有些隨興所至,詩作都是他幫忙整理、歸檔。」已經完成卻沒有出版,不覺得遺憾?她搖頭:「《戀人狂》是我們的愛情風景,我們的祕密絮語,它本來就不會向外。我們也不是堅決不出版,只是沒動過念頭。裡面有些詩也發表在副刊詩刊過。如今回頭去看,裡頭的作品有些是不夠成熟的,真要出版,該改寫或重寫。這麼一來,又好像不是2013年一起寫完它的原始心情。」
▉《潔癖》:維護自身,對抗世界的證據
詩人如巫,由於奇異的敏銳,林夢媧的詩歌,即使處理的是可見的日常,但內裡都是深邃的生命驗證,「古代巫者的詩歌,其實就是與神溝通的語言。但我覺得現代詩不會是祈禱,而是人為選擇,是對事物的記錄,是詩歌真正發聲的時刻。」
林夢媧也說道:「我感覺心靈像是一頭豹,那是充滿速度的情感狀態,但無法顯露,總是在蟄伏,關鍵時刻才啟動。豹是獨居動物,牠擁有孤獨,但環境適應的能力強,懂得保持行蹤隱密,我也在做同樣的事。」豹時速可以達到60公里,獵殺動作優雅而殘酷,但林夢媧最有感應的是牠瞬間停頓的能力,「豹的極速運動狀態與具備力量的靜止,跟我的內心是吻合的,特別是對外界的憤怒與及自我壓抑。女性一直被要求必須打開自己,不能拒絕被進入,從生理器官到心理狀態都是如此。我無法苟同這種奇怪的社會價值,但從小到大又都被迫要練習停止內在的凶猛往外噴發。」
「豹是精準無比的動物,牠的精準表現在殺傷力,每個動作都善盡肌肉與神經的配合。」林夢媧表明:「我的精準,則是體驗在詩歌上的簡短主義,我想要達到最快的速度,以及最精微的激情。」
嚴格來說,《潔癖》才是林夢媧第一本詩集,收錄2013年到2018年的詩。何以《潔癖》無分輯?「分輯就像將詩集再細分好幾類。但潔癖本身不需要分類,它是一體的,是我的日常切片,全部是獨立且完整。」
「我沒有刻意進行主題性創作,只在編選時將適合的詩歌放入。」林夢媧強調,「我有滿嚴重的潔癖,喜歡乾淨,常有排除其他人的激烈慾望,包含家人,只有戀人是例外。」她不能忍受骯髒,任何身上與房間的不淨都會讓她焦慮。「比如去外面上廁所,男生沒有困擾,好像到處都可以。但身為女性就得忍受各種不潔。」不止是視覺上的污穢讓她卻步,氣味也是,「有些根本是還沒有看到,光鼻子聞,我就踏不進去,只能全力憋住。」林夢媧苦笑。
她表示,「為了維持內在的秩序,我必須對外界展現潔癖。潔癖是無力感,因為世界並不會為你改變。我能做的只有在周邊建立結界。所以,潔癖是對抗的方法論,潔癖是圓圈,暗自不斷變大的圓圈。」林夢媧總想要讓環境更乾淨,卻會讓自己更疲累。在屏東時她經常掃地、拖地,一根頭髮、一點汙漬都無法容忍,但他人無心保持,經常才做完打掃,轉眼地上就是泥印,且周遭人會理所當然視整潔事務是她的責任。潔癖反而使她受困其中,更被無用感痛擊。
後來,從屏東搬至台北的城市落差,林夢媧也得努力適應,「空氣和水質都不一樣,會有在廢氣中呼吸的感覺,交通更恐怖,巨數量的景象,再加上台北生活的速度,我無所適從。我得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全新的人。」結婚後也發現,丈夫雖會讓身體保持潔淨,但居家環境卻雜亂,「我會幫他整理,但他會異常焦慮,尤其是當需要一本書,卻不在原來位置,戀人幾乎要把這間屋子翻過來。」林夢媧一臉無奈,「我想要創造自己喜歡的秩序,但現實不是這樣運作的,我需要調整自己,所以潔癖圈有時也會縮小。」
懷孕後,林夢媧的感官能力被擴大,「感覺像是擁有兩個鼻子、四隻耳朵,嗅覺與聽覺非常靈敏,一點氣味、聲音都會讓我嘔吐、頭痛。生產因為吃全餐的緣故,」全餐即是催產、陣痛、手術等經歷,讓林夢媧如同被徹底改造過,「身體脫離我的控制,不可掌控的感覺更強烈。生完小孩後,容易厭世。對我來說,把自己削剩到十分之一,就是媽媽,」林夢媧無意圖美化母親的定義,「其他的十分之九,全是小孩與生活。我喜歡自己的女兒,喜歡和丈夫一起經營家庭,但裡面有很多掙扎,對自己還能不能是自己,能不能是女人,十分憂鬱。這些漫長的細節,需要日復一日的消化、陪伴與渡過。」在各種無力經驗的衝擊下,林夢媧不想坐以待斃,所以潔癖更演化為自我整頓的功能。
林夢媧慢條斯理地講述:「寫詩也是潔癖的表現,它是關於整理的整理,是將我的潔癖收納在詩歌裡。人生難以言說的陰暗、骯髒與錯亂,我都會寫進去,但用字是乾淨的,我喜歡它是整潔的,不多不餘,必須是精準的收納術。而所有日常都是詩歌的來源。我找到這樣的方式,安放生活無止境蓬勃的髒亂。《潔癖》是維護自身、對抗世界的證據。」
林夢媧以詩意的目光逼視女性內在的混亂與無助,她的空靈感,帶著暗影與傷痕,而詩是她對無序世界的整理之術,是心靈對外在環境的抗衡,是安放結界的奇技淫巧。唯獨如此,林夢媧方能夠保有自身的獨立與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