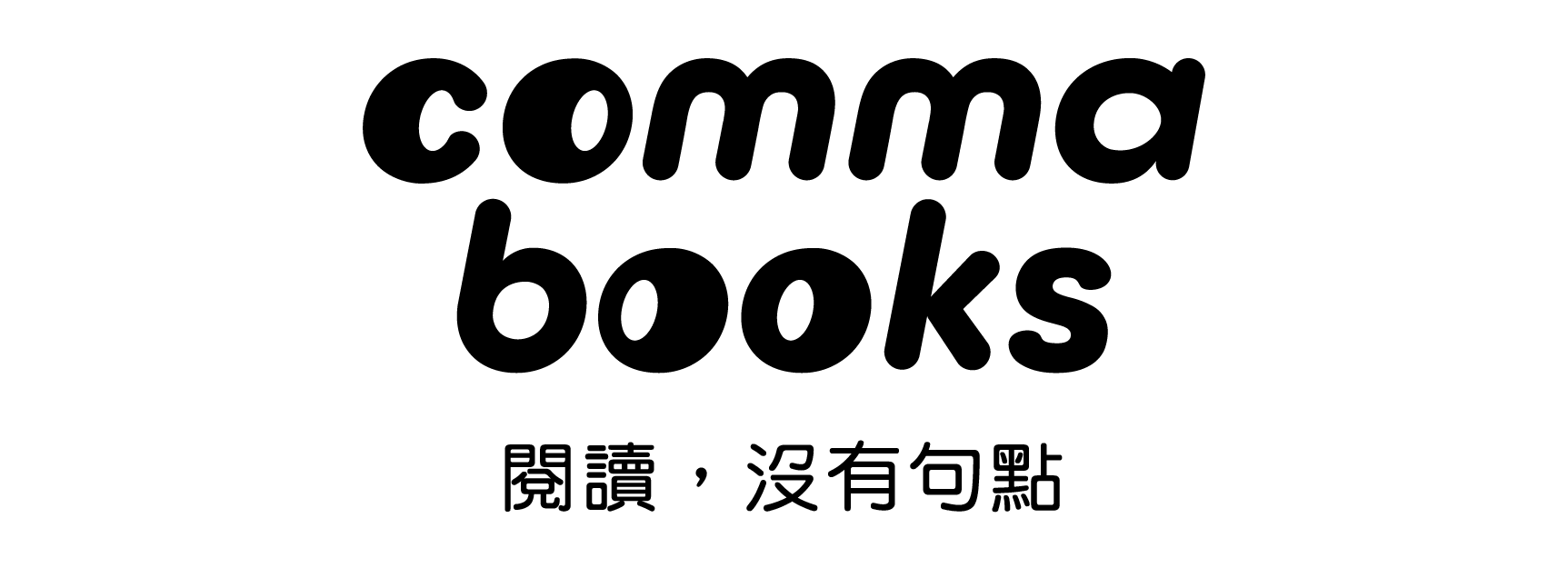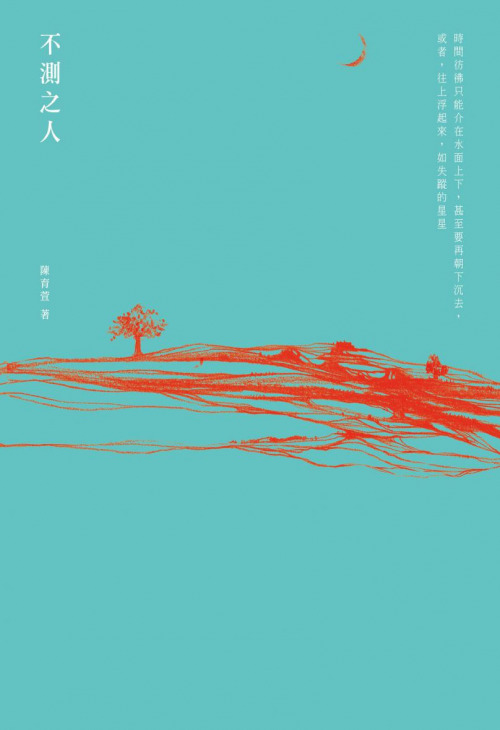「一切都以臺北為中心,但南方觀點呢?」——專訪《南方從來不下雪》陳育萱
小說家陳育萱2015年出版了大獲好評的長篇小說《不測之人》,時隔5年再推出短篇小說集《南方從來不下雪》。從臺南、高雄回返到故鄉彰化定居,陳育萱對南部又有更多理解與認識。在新作裡,陳育萱寫出她所體驗到的南方野境世界。
▉對自由的渴望
自稱原生家庭是中規中矩、高中以前都生長在彰化的陳育萱,一直覺得被家鄉困住了,活在絕對封閉的世界,好像不會有任何推進,日常總是一成不變,心情甚至會是煩躁的,但少年時又只能順和環境,無法有何作為。陳育萱說:「小學5、6年級有被霸凌的經驗,但又不明白自己為何會被針對。國、高中並沒有悲慘的遭遇,但就是覺得跟大家有隔閡,沒有推心置腹。所以後來舉辦的同學會,我一概都不去。」
對當時渴求離開彰化的陳育萱來說,閱讀是最好的自由方式,包含李欣頻的旅行書,也為陳育萱帶來生命的彩度,並埋下她日後熱愛旅行的種子。而高三的國文老師,會在期末分享書單,譬如張愛玲、楊牧、老舍、沈從文、郁達夫等,對陳育萱產生頗大的後座力,其中特別受張愛玲吸引,先從《傾城之戀》、《第一爐香》等短篇讀起,再往長篇與評論發展。陳育萱眼底有光:「相較於楊牧或沈從文往內深縮的寫法,張愛玲是外顯的,文筆和場景的設計都十分驚人,對人性醜惡面的凝視也很誠實。而且,她的文字本身就是華麗的展示品。我直到大學都還喜歡張愛玲,也很在乎文句經營,有點像是要求自己必須造出一個完美的玩具。」
另外,陳育萱雖然也參加文學營,但關於臺灣文學,陳育萱自言起步甚晚,包含同為彰化人的賴和、楊守愚等,都要很後來才曉得他們的存在。大學時,陳育萱就讀師大國文系,陳育萱明白地講:「它很傳統,學習環境閉塞,而且要修的學分滿多,可以向外探索的時間有限,可是相對於國、高中,已經是好太多了。」
她亦透露出如果可以更早接觸文學創作的話,或許一切都會更不一樣的遺憾。她自認是晚熟的,要到研究所時期,才開始小說書寫,在那之前所寫的不過是習作,沒有抵達核心,找不到自己真正關心的主題與方向。
▉畸零與邊緣的視角
考上東華創英所後,陳育萱推遲一年就讀,先順從家人的希望,回彰化實習。但她的嗓音裡帶著餘悸:「太可怕了,我幾乎像是落荒而逃,遠離了教育現場與彰化,到花蓮展開美好生活。」
東華的小說課,在許多方面也影響了陳育萱,李永平與郭強生的教授,讓她更能夠掌握自己的語言與小說精神。其時所讀的如馬克.吐溫(Mark Twain)《湯姆歷險記》和《哈克歷險記》、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小城畸人》、芙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智慧之血》等,都是文學養分,「浪遊的角色和冒險的精神,還有畸零者的邊緣位置,乃至底層社會的樣貌,讀多了以後,我就開始有想寫的驅動力。」
陳育萱視為第一篇小說創作的〈凝紅淚〉就在東華時期誕生,內容是移工與公安意外的故事。她頗有自覺:「我最初就想寫弱勢族群,也是後來兩本書的主要書寫對象。他們沒有太多資源,甚至一再受劫,生命充滿無可奈何。」
《不測之人》與《南方從來不下雪》是陳育萱的南方二部曲。《不測之人》的場景設在仁仔溪、陂仔尾、關帝廟,題材則涉及農村生活、貧窮疾病、鐵工廠、宋江陣等,對白是大量的臺語,鄉間感濃烈。陳育萱透由新死之鬼不斷徘徊在水域裡,同時記憶潺潺而動,穿梭於幽冥之時與存活昔日往事,帶出南方異境,也就令人要聯想到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迷宮中的將軍》的大河之旅、莫言《紅耳朵》那些奇異癲狂的山野異譚乃至李永平、張貴興等馬華作家小說中常見的河流及雨林意象,同時又對應到臺灣新鄉土書寫如陳雨航極其可貴平淡視角下的《小鎮生活指南》、林俊頴國臺語雙聲調敘事並行的《我不可告人的鄉愁》、童偉格充斥死亡與創傷的《王考》等。
「人必然會受到地域的影響,你活在哪裡,自是不可避免帶著那個地方的氣味與習慣。」陳育萱轉而提到這十幾年間,從在花蓮讀研究所,到臺南的家齊女中與港都高雄的高雄中學教書,於南方棲居了七年之久,於2017年才返回彰化。而在臺南與高雄的所見所聞讓她寫下南方二部曲,「我想寫南方,是因為南部是被臺灣進步發展下的犧牲,不管是經濟至上或政策設置,大多是犧牲南方的生活條件與自然環境,來成全北部的需求。南部在各方面都遠遠不及北部。」
她提到港都雖也有機場、捷運,但各種建設,包含女工權利、工安議題、環境安全,有問題的比例都偏高。陳育萱以空汙嚴重為例,「南部人卻罕有戴口罩,明明空氣品質非常可怕,但每個人好像都習慣了。那種把不正常的狀態視為正常,非常弔詭、荒謬。南部人所在的現場,他們生活裡所經驗的種種不公平應該被看見。我希望衝破侷限,把南方的生命困境、社會真實樣貌呈現出來。」
▉說南方,哪裡是南方
向陳育萱提問時,她往往會像是忽然憶起什麼似的「哦」的一聲,眼睛猛眨、認真思索後,方才接續回答,模樣可愛。而喜歡國外旅行、厭惡封閉氛圍的她為何會想回到彰化?陳育萱臉上冒出費解的神情,「是啊,到底為什麼呢?理由我也不清楚,或許是因為在外頭獨自生活了十幾年,覺得想家了。」頓了頓後,眼底的迷惘置換為清亮,「但也帶著能重新創造一個適合的環境的信念吧。」
陳育萱表示,雖然不至於後悔,但搬回故鄉後,極度震驚:「因為彰化的整體環境還跟我少女時期一樣,停滯於原先的位置,沒有任何改變,相當不可思議。」她是失望的,但沒有絕望,現在的陳育萱有一群友伴,在彰化致力於推廣文學與藝術,實踐地方創生,「彰化有賴和等作家,曾經它是一個著名的文化場域,如今雖然不復從前,但我們都相信,彰化值得被看見,有再起的可能。」這也就令人期待,回鄉生活的陳育萱日後會開展以彰化為場景、主題的原鄉小說,如其師輩、同是彰化人的林俊頴傑作《我不可告人的鄉愁》。
而《南方從來不下雪》描繪的故事都發生在高雄,但南方其實何止於港都──南方以南,也還有更多南方,如陳育萱所寫的移工們來自臺灣的更南方。南方是相對性的地域,南方應當是一種脫離主流視野的精神,像她喜愛的美國小說家們威廉.福克納(Willliam Faulkner)、卡森.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芙蘭納莉.歐康納等,盡皆書寫美國南方的故事。那是一種跳脫慣常的核心思維,找到邊緣的野性之力,凝視苦難的現狀與探索起源,不理所當然中心化的敘事能耐。
唯陳育萱並非以小說施行控訴,而是更普遍性地去看見南部被長期漠視的現實,「我們一直以臺北為中心,一切依據北部價值運作,這本身就不夠多元。」陳育萱語氣凝重:「但南方觀點呢?南部人的心聲該何去何從?在我的感覺裡,南部就像不被看重、遭受壓抑的野小孩,會做出什麼樣荒唐離奇的舉動,非但無從預測,最後生長出反向的力量,好像也不意外啊。」
同時,陳育萱也將對高雄的心意寄託在《南方從來不下雪》,她動情講道:「像是為了告別南方而寫,說它是一本告別之書也無不可。我在港都的那段時光,是我人生的黃金歲月,人事物持續不休地滾動,我確切有種沒有辦法再重來的心情。」
▉如果還有一點光
因拍攝視覺企劃的需要,本次專訪在前進中的火車、月臺上、車站大廳裡進行,一方面契合陳育萱自稱的「旅行總是能讓我再找到生命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暗指其小說的遷徙調性,不僵固,人性始終保持柔軟的移動能量。而陰沉的天色下,偶爾有日光鮮豔短暫地灑落在陳育萱臉身,也十分貼近《南方從來不下雪》大塊暗黑籠罩有些許光亮閃現的閱讀印象,就像是枝裕和的《幻之光》,整部電影都陰灰暗沉,丈夫驀然自死的女主角也身著黑衣猶如服喪,直到電影尾聲終於有好天氣,陽光普照,亮著整個海灣、漁村,而女人翁穿著白衣藍裙,彷若從死亡創傷裡緩步而出。
《不測之人》傷悲的語調、陰翳的氣氛、慘絕的現場,來到《南方從來不下雪》後,就變得明亮,文字使用更都會感,背景也從農村經驗轉移到工業社會,挺進各種文明災害現場,包含高雄氣爆、白色恐怖、水災、工殤、都更等社會議題,並且細膩地鋪陳各樣身心創傷後症候群,兩本小說在許多方面顯得截然不同。陳育萱說:「《南方從來不下雪》裡的小說,經過多次的修改,尤其是2019年暑假後的增寫,它們才長出應該長出來的樣子。在那之前,總覺得缺少決定性的東西。現在的版本,情感方面與小說層次方有達到我心中的標準。」
書寫有時候頗為倚賴機遇,譬如〈放生〉寫老兵,陳育萱笑著說:「有時候就是很剛好,一開始我就設定寫黃埔新村,做功課時赫然發現這個眷村跟孫立人頗有干係,而且也有白色恐怖受害者,一下子就全都連起來,交織成複雜的面貌。」
此外,陳育萱以為,與讀者溝通很重要,如果從臺語文的運用,移轉到一般人較能夠接受的文字範疇,是比較好的,是以《南方從來不下雪》在人物對白做出調整,未如《不測之人》式以臺語聲腔為主。陳育萱滿臉誠摯地講著:「這並非意圖討好讀者。我也認為,重視母語的消亡是十分重要的。但現階段的我,想要讓更多人來指認、核對彼此心目中的高雄。我滿想知道,自己所感受、體認到的南方,跟大家所知的是否相近。」
由於搬離港都的緣故,拉開了時空距離,讓陳育萱乃能以小說清冷地透視她的高雄記憶與生存景觀,不陷入當時當地的激情。她悠慢地說:「再平凡無奇的人,都有他們各自的故事。文學能有足夠的耐心去瞭解他者,但我絕非要代言。將南部確實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用小說展演,在虛構與想像中找出同理心的可能,不僅僅是新聞、數字或者批評,我相信這才是小說所能做到最好的事。」
「苦難是有意義的,人得遇到強烈的挫折,被巨大的命運之手下碾碎,遍體鱗傷後,才能有徹底的轉變。」陳育萱深悉,創傷其實從來無可療癒,人只能接受與適應來到面前的各種事物。這也是何以《南方從來不下雪》每一篇都在直指生存的哀慘艱困後,有著淡遠的結局,人物們皆帶著未曾痊癒的疤痕,在暗灰人生中,持續抱持如果還有一點光亮的盼望,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