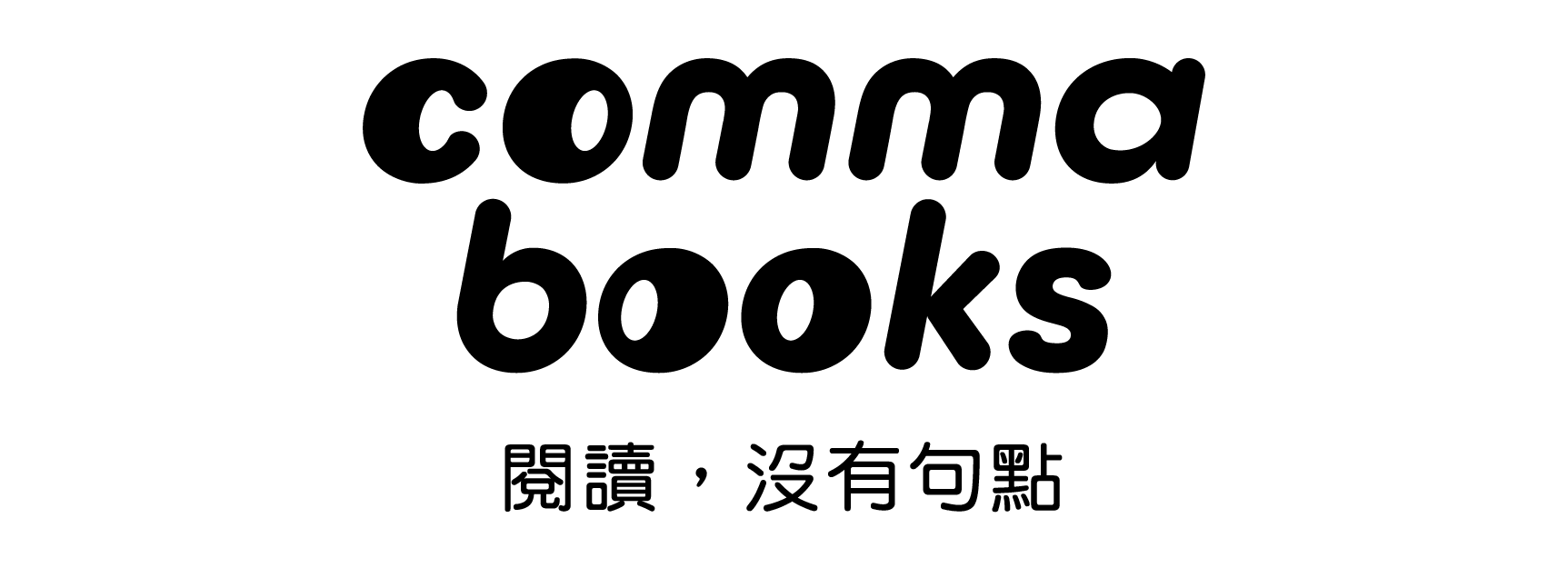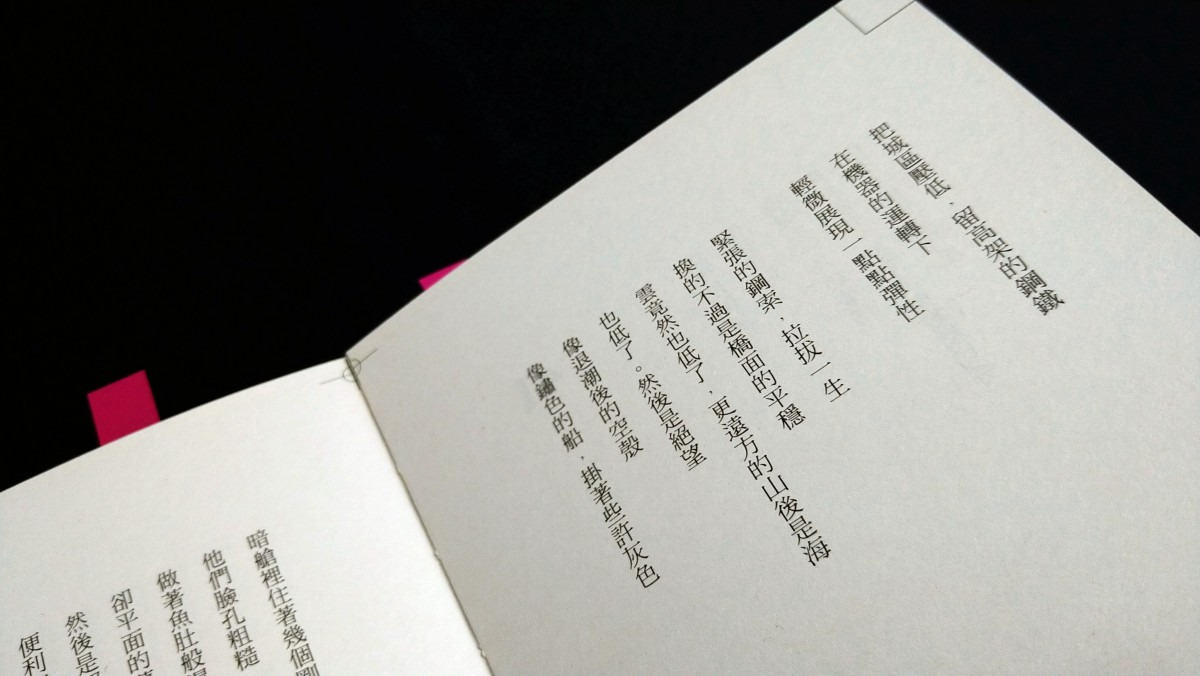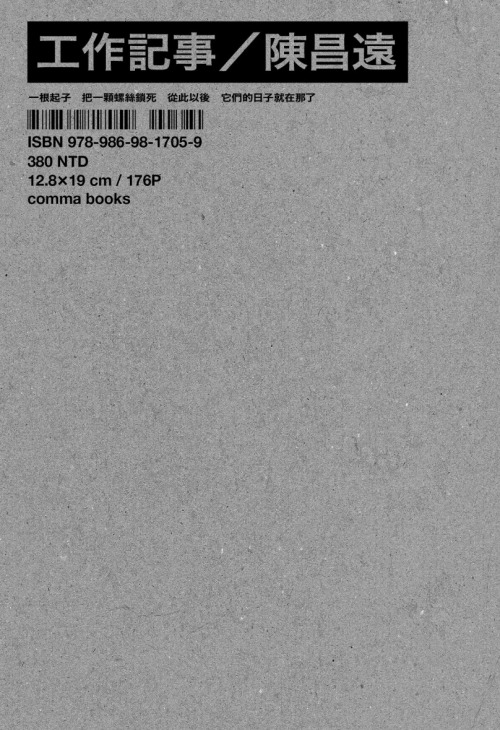留高架的鋼鐵/在機器的運轉下/輕微展現一點點彈性。陳昌遠:「我喜歡到高處觀察高架,感覺一整個城市因為這些高架而有了血路。」
《工作記事》作者陳昌遠,先前曾是報紙印刷廠技術員。他的朋友這樣介紹他:「這個人很屌,他寫詩,但是投副刊都投不上,所以他就跑去印副刊了。」報紙印著印著,技術員成為了一名詩人,並出版第一本詩集。逗點邀請陳昌遠撰寫他在印刷廠寫詩的種種故事,第九篇,他從談了初初來到台北的不適應、在報紙印刷廠內遭遇到的不愉快,還有那些在油墨與噪音中共事許久所產生的同事情誼。
「快夜了竟然還有風/把城區壓低,留高架的鋼鐵/在機器的運轉下/輕微展現一點點彈性」(工作記事-41)
剛到台北工作時,常常騎錯路,有一次在中永和一直迷路,花了二小時才過橋接到基隆路,也感覺這裡的人騎車真的是充滿殺氣,很會鑽,曾經算過自己一天在基隆路上被超車的次數,超過一百次。我太習慣高雄的大路,以及小巷小街的鬆緩懶散騎,即便在台北街頭機車穿梭三年了,我現在仍不習慣。
台北市區有許多高架道路(或捷運軌道),常給我一種巨大的堆積感,砌造感,組建感。那灰色感與高樓大廈冷硬不同,有點彈性感。有時我會望著,注意上方車輛行經的燈光,期待能感受一點點震動。
我更喜歡到高處觀察高架,感覺一整個城市因為這些高架而有了血路,那些車輛都是運作的液體。有時望著公寓的窗,會想起七歲時的風景,無聊不能出門,整個下午就趴在窗邊,看車來人往,看對面公寓的鐵窗。三十年過去了,我仍在看著鐵窗,想著有些人工作一輩子,就如鐵窗一樣框在那邊,日曬雨淋,一輩子鏽。
離開印刷廠二年後,有一次回高雄找了離職多年的老同事閒聊,他說,大家都以為你會在那邊做滿二十五年退休,若要說誰真的會離職,沒人想認為是陳昌遠。後來他又說,現在要你回工廠,你大概也回不去了。我聽了之後,一時間也不知道該回他什麼話。
突然想起印刷廠的第一任廠長,因為看不慣我留長髮,要我剪平頭,我只為了工作安全修了瀏海,仍是綁著馬尾,他質問我,我辯解,這忤逆被他記住,後來就不讓我升職等加薪。所以我做了十年只從三級升到一級技術員。按常理做了十年應該升技佐才是,我很不爽,後來工作就懶散打馬虎,我相信機長都看在眼裡,但他們也不在意我裝死,反正有把事情做好就好。
記得離職前,我跑去告知第二任廠長,想說要走了,有點禮貌先講一聲,去辦公室找他,他坐在辦公桌前聽了就叨唸起來,說人來人去,印刷廠待遇不錯,何必走,我說有個機會,總要嘗試一下,他說有什麼好嘗試的,一堆人離開印刷廠也都在嘗試,什麼哪邊錢比較多,哪邊多涼,最後還不是想回印刷廠,出去就不可能再回印刷廠了,我們不會回聘離職的人芭拉芭拉的。他嘮叨了一堆,也沒打算拉張椅子請我坐下,真的很那個。
我聽他在那嘮叨,就說已經決定了,禮貌上告知,感謝你照顧,就這樣。其實我內心有許多不爽許,曾經跑去修在職專班的工業管理,工廠的工作教育很殘缺,一些安全管理之類的只教個大概,機器原理與結構連皮毛都沒教。我去讀在職專班的事被這第二任廠長知道,洗澡間洗澡時,就見他一邊對著鏡子刮鬍子一邊說,公司薪資只認進公司時的學歷,不認後續追補。我其實想的不是加薪,而且也讀得不是太開心,因為我從小到大都不喜歡學校。當下聽了雖然內心不爽,但也懶得回嘴,悶著就算了。說起來,人為何會對階級有恨意?那是因為意識到階級的差別。如果沒有意識,對於階級不會有太大的反感。
我素來不喜歡高層,有一次處長來,彼時印刷廠人事不穩定,老得太老,年輕的太年輕,怕年輕人離職,處長約見一眾年輕印刷員,講話噗拉噗拉的,反正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離職,我擺老跟處長槓起來,說加薪起薪太少,做大夜這樣的薪水不值得,大家年輕都會想加班拚錢,這裡沒這機會。處長三言二語打發了我,後來其他同輩印刷員稱讚我很屌,敢跟處長槓,說實在的我也只是日子苦悶,有個機會槓高層就槓一下,反正我沒打算當幹部。
離職時,黃機長跟李機長很體貼,不約而同私下要我別遞辭呈,改成請二個月的長假,他們擔心我到台北工作若不習慣,或不適任被開除掉,那印刷廠沒辭,還算有個退路,若真做得慣,他們再幫我遞辭呈。這是很有人情味的策略與建議,但我拒絕了,覺得既然要走就乾脆點。我至今仍感謝他們的好心,很溫暖,是同事之間在油墨與噪音中共事許久所產生的情誼,就顯現在道別的細節裡。
雖然我是二年後才想明白。
(寫到這邊想起參加中時罷工投票的回憶,那真的是讓我明白了什麼叫做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