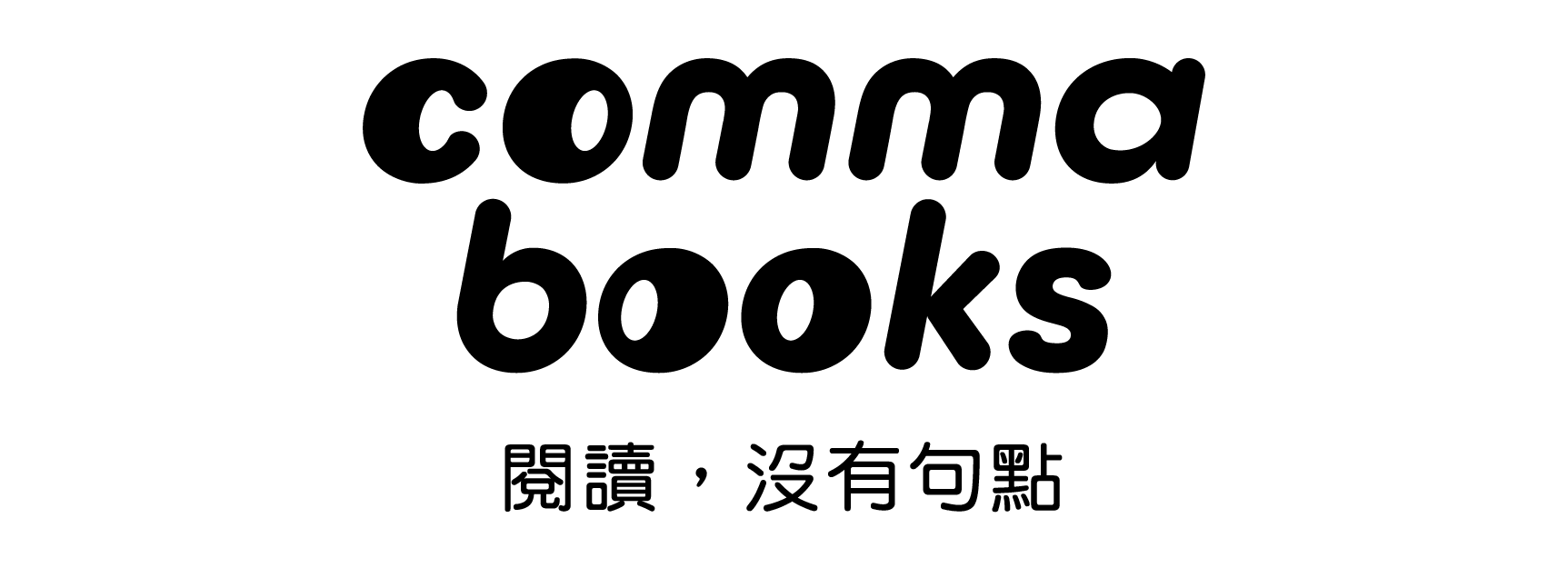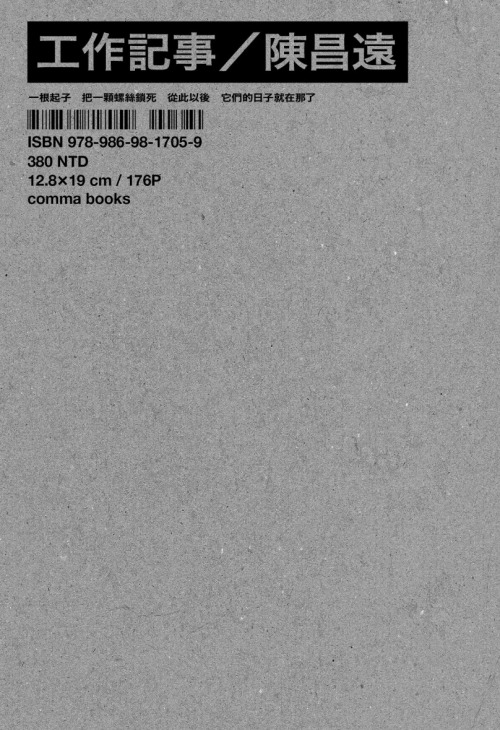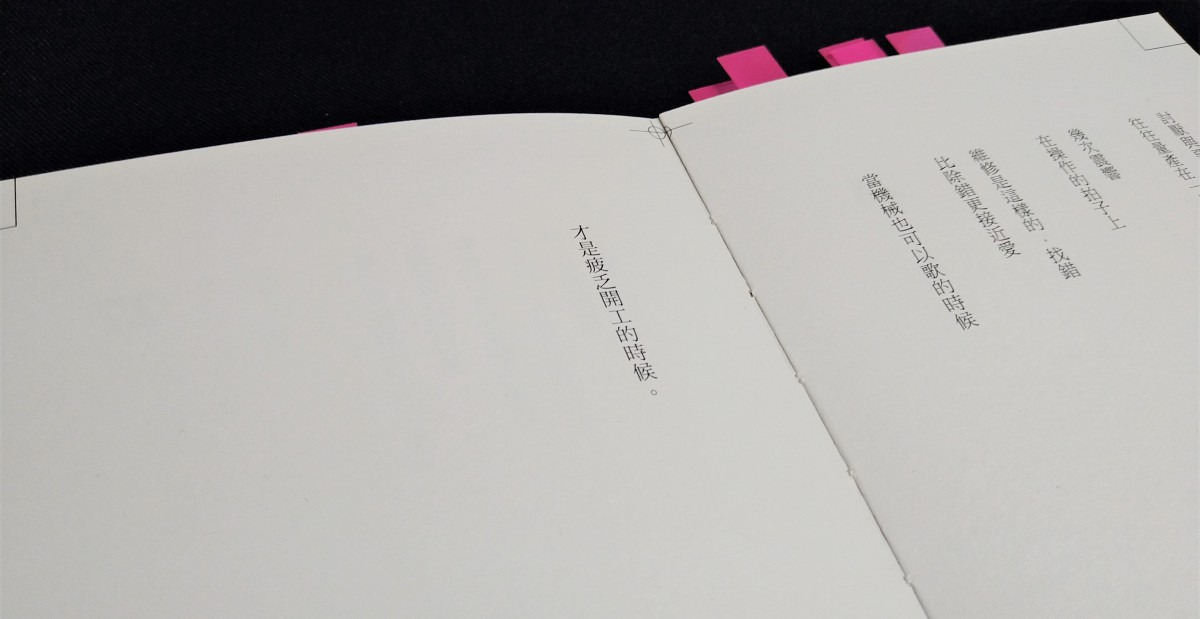
當機器也可以歌的時候,才是疲乏開工的時候。陳昌遠:「我在機器旁邊的置物櫃,用厚紙板做了個盒子,盒子裡固定放三四本書。」
《工作記事》作者陳昌遠,先前曾是報紙印刷廠技術員。他的朋友這樣介紹他:「這個人很屌,他寫詩,但是投副刊都投不上,所以他就跑去印副刊了。」報紙印著印著,技術員成為了一名詩人,並出版第一本詩集。逗點邀請陳昌遠撰寫他在印刷廠寫詩的種種故事,第十篇,他談到報紙印刷廠內,不只是在空檔閱讀,他也總在機器運轉的噪音中想著怎麼寫詩。
「當機器也可以歌的時候,才是疲乏開工的時候。」(工作記事-26)
當印刷穩定,或者等待降板的時候(報紙印刷需等待記者最後的截稿),我會開始想別的事。我在印刷機旁邊的置物櫃,用厚紙板做了個盒子,盒子裡固定放四本書輪換著讀,有時一本書我會重複讀很久,例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我喜歡裡頭那個無能男人碎念的樣子,那些無謂的自我懷疑與抱怨,顢頇樣貌,都跟我很像。另一本是《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林燿德的小說與詩集,還有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
很多時候我在想詩要怎麼寫。機器運轉時戴著耳塞,但噪音一樣擋不住,可是噪音持續的狀態下我會感受到一股安靜,機器在那邊轉,橡皮滾筒,裝版滾筒,膠輥油墨,在彼此緊黏的狀態下轉著。毛刷刷著水也在轉著。而紙張從一樓經過過紙輥,一路跑四樓高處,再進入三角板,裁切,折疊,最後到達輸送帶被我抽出來檢查。
想到一些詩句的時候,我會寫在廢紙上,等到下班回家就丟在雜物堆裡,隔一段時間再做整理,把這些零碎的句子拼裝成一首詩。
颱風天老家淹水,這些草稿放在箱子裡,因為泡水全黏在一起,發了霉,又乾掉。這讓我有一種那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這樣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