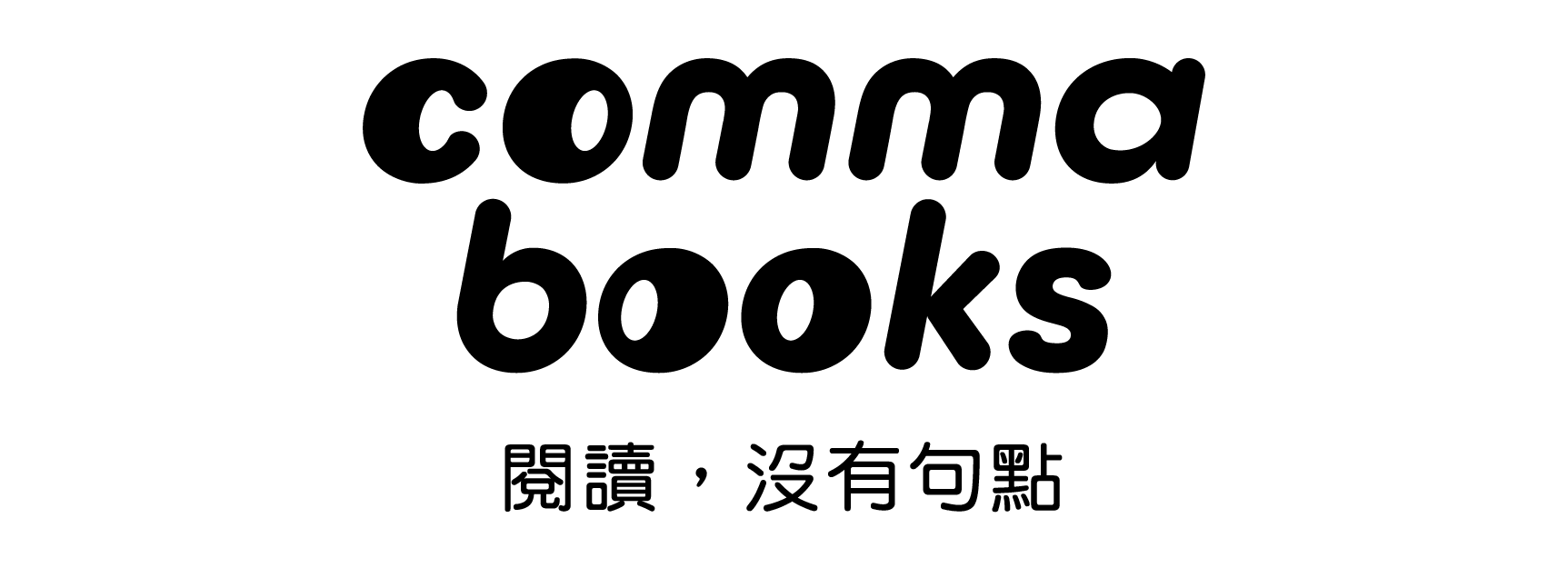陳育萱《南方從來不下雪》〈放生〉(上)
二零一八年冬.高雄
鄧文成終於決定要放生他的狗。
是日,南方難得陰沉的天色下,他搭上公車,一路向海。
時間流淌到盡頭,乘客一個一個沿線下車,他略駝的背還種在後門邊的座位上。司機透過車內後視鏡瞄了他幾眼,而鄧文成只是盯著跑馬燈,閃著紅光的站名一遍又一遍出現又消逝。
這條路線,很長。
「爸,就這樣說定了,您下個月得來美國,不能再讓您一個人待在那棟公寓裡了。」話筒另一端是他的大兒子。
「什麼?」鄧文成提高音量問道。然而,後續的回答越來越模糊,到最後一個剎止,與兒子的對話瞬間消散,現在耳畔重新盈滿彷彿來自遙遠彼岸的海潮,潮水淋上他脆弱的耳蝸,在神祕的通道裡製造聲響。
最近鄧文成越來越困惑於清醒的定義。
自從醫生宣判老年性聽力退化的那刻起,他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時不時被夾成片段,而後猶如醒自一個很小的盹,困惑地發現「現在」才是真實的。沉溺於半夢半醒間,無法順利開口描述這荒謬經驗讓鄧文成只好力圖鎮定地坐穩診療室的圓椅,虛心向醫生詢問診療方針。
「不要抽菸,不能喝酒,少油少鹽,盡量保持運動習慣。」唱念完這串,醫生低頭看病歷,頓了半晌說:「感覺神經性聽力受損基本上沒有特效藥的,不過,我建議可以先試著配戴助聽器,效果應該你會滿意。」
「助聽器?」鄧文成重複道。確實這一兩年經常聽不清楚對方的說話內容。然而,聽到宣判的結果讓他仍感一陣刺痛打擊。又來了,心情一旦低落,詞彙「助聽器」遂逐步瓦散於聽覺範圍之外。
醫師熱心地為他解說助聽器幫助聽力復健的原理,並且向他推薦幾款價格合宜的機型。鄧文成的背挺得直,保持禮貌或下意識顯現不願屈服病魔般的意志前傾聆聽,盡可能捕捉字詞,將它們一一送回該有的位置。不過,醫生熱切的程度早忘了維持初始的語速,雙脣快速鼓動。他努力捕撈醫生嘗試解釋的一切,然而所有事情都像是漏網之魚,直到醫師轉身密集敲打鍵盤前,鄧文成終於聽懂—「我還是開給您一點維他命,讓鄧叔您晚上安神好睡……。」
如同所有電影螢幕浮出「劇終」二字之前,仍須對於任何冒出劇情逆轉的危險潛伏因子提高警覺。等著藥方的空檔,方醫師打字聲大如雷響。聲音在耳畔間雜了鞭炮聲與恭賀聲,他猶熟悉著舉杯時的心情—這是咱村裡第一個考上醫生的!
—門口嗡蠅般道喜聲,那些高高托起拿手菜跟賀禮的手。老方一家準備小菜和高粱,男人們一夜醺醺然,輪番瞅著、拍著老方那瘦巴巴,穿制服像掛在晾衣竿子上的兒子。老方兒子戴眼鏡的臉掩不住高興,有點怯的性情,在這一天格外忙著叫叔叔、伯伯好,還替夾菜,自己的碗筷則壓根沒動幾次。鄧文成瞇起老花眼,以眼丈量身著醫師袍的豐實下巴和膨皮而略油膩的臉,腦中幾度比對。
—那剛考上醫學系的少年臉龐究竟長什麼樣?這麼一想,竟陷入模糊變動的苦惱裡。哎,想起了也不如何。
「這是終點站,終點站—」
公車司機倦響的通知讓鄧文成破出回憶幻想。車門敞開,他跟狗都下了車,只是狗比他還早聞到菸味,鼻端皺成一節,四肢如馬蹄四處輕踏,狗在頸圈的限制下,盡可能離菸味遠遠的。
「來一支?」鄧文成搖搖頭,年輕在軍隊試過一口。打仗時,菸貴得跟金子一樣!第一次貪心地吸一大口,嗆咳老半天。抽菸的第一次經驗讓他後來每吸必咳,更做不來學不成宛如大明星般瀟灑的吸菸動作。
司機抽菸姿勢不怎樣,速度倒快得很,沒多久把菸屁股踩在皮鞋底下。鄧文成的黑狗湊上前去,對著冒出星火的菸氣低吼了一長聲。
「這是土狗嗎?」
「噯……不清楚,牠小時候我們在門口盆栽旁發現牠的,我太太堅持要養。」他向司機比劃黑狗最初的長度。
「帶牠來海邊散步啊?」發車時間還沒到,司機又點了一根菸。
「嗯。」狗的胸膛十分飽滿,坐得直挺挺的,尾巴輕搖。
這兩人所在的濱海小鎮除了低矮平房,尚有幾排施工搭建到一半的透天厝,宣傳的廣告看板矗立在旁,在夕日輝映下,色澤褪去之故,透出隱約破敗氛圍。
「家住這邊喔?」問話漫不經心,司機看了看錶,逕自上車,看樣子隨時準備啟動,似乎不期待獲得回答。
「不是……」他遲疑著,因想不到更好的理由而沉默。
司機沒有追問便關上車門。公車在荒草地上迴轉,車輪抓地,揚起一陣風吹沙。拜他的聽覺再次遮蔽所賜,鄧文成沒有理會公車因老舊而發出的軋軋聲。
隨公車離去,黑狗小寶開始大力搖動尾巴,提醒散步時間到了!鄧文成俯身摸牠的頭,憐愛地看著邁入風中殘燭的狗,牠的老態使他這一兩年特別容易思緒跳躍。這幾年走掉的同袍,十幾位啊,接二連三的,不少是戰役落下的病根糾纏。當年的少年兵忍著不死,只為了從血海戰場掙扎回家。回家的信念讓人勇敢,再惡劣的環境,能放進嘴巴的全吞下了肚。鄧文成憶起餓到神智昏聵的一晚,吃下了同袍遞來的一碗狗肉。從生死關頭醒來後知道這件事,多想澈底忘了……縱使成功忘卻,卻改不了鐵打的事實。
散步時間,牽著小寶來到盛產烏魚的水鄉,冬季的風一吹拂,鼻端盡是濃重腥味。不去公園,牠看向某個方位又看向他,拉扯頸圈的動作中,小寶似乎感覺到不同,靜靜地垂下頭。
鄧文成也好不到哪裡去,他顯然打壞了節奏。
他想前往海濱,依循印象牽著小寶遊走於各個應能叫得出名字的路口,左轉右踩,盡可能朝遠處極目而視,獲得的卻是輪廓不甚明白的灰影。所見民宅千篇一律藍色鐵捲門,頂樓加蓋的淺綠波浪鐵皮成浪,牆面滿布細小綠色磁磚,破損處處。單調困難的機車引擎噴出一管管黑煙,障蔽空氣;藍色小發財車忙著卸下漁獲,吆喝搬運。等在家中的人必須在成批已然死去的雌性烏魚體內拿取她們的子嗣。
一網袋一網袋地任魚群互相擠壓,在空氣中一步步失去水分,失去存活的條件。她們的身體一旦上岸,就沒有完整的必要。取卵、綁線、清洗、去血、鹽漬,置放於木板,反覆壓實壓平,在勁風與烈日交替作用下,成為一片上好的烏魚子。賣出好價的烏魚子,通常不是搬運或製作的人吃得起。妻子出身在這,童年或少女時代卻沒嘗過。
他第一次見面時閒聊起哪一間製作的烏魚子好吃,她說因為不忍吃魚卵,這類訊息一概不知,他不知這是委婉,把這事記得特別清楚,往後去餐廳,不點魚卵,唯獨後來謹記完整的人還是他。妻子絲毫不感歉疚地活進平行交接的所在,在那裡活得更長,連小寶她也忘了。
他還能說什麼?
鄧文成感到胸口緊悶,彷若誰把微駝內縮的胸口狠抓一把,旋緊,讓心臟不由自主地空停一拍。廣播主持人重複的警告看來沒錯,這幾年南方沿岸的空氣汙染特別糟糕,PM2.5對應的指標顯示紫爆。少壯時拔尖到天不怕地不怕的體格,現在對空汙過敏起來,說起來她會笑自己的,鄧文成想。
一九四二年冬.廣西靖西縣
告別廣漫的惡土成為他十六歲的成年禮。
他的老家,上天只偶爾降水,水朝地面下走,形成伏流。留不住雨水的土地蕭瑟是乃歉收的季節永遠養不起下一季的希望。雙腳所踏淨是破碎地貌,深長岩溝與容易使人絆跤的窪地。
前幾日,地主又來討租金了。
老家前門直通後門,狹小如斯的空間要價不斐,得變現作物三分之一價,才付得起虛晃不實的浮濫租金。地主越來越喪失耐心,某個傍晚,來了一群人不由分說砸爛了屋子門窗。
流氓胡鬧完的那晚,他給姥姥裹上所有被子,深怕她受寒。只是心頭越憂慮,風就越在耳邊聒噪,在灰壁與破窗之間如幽魂呢喃。隔日醒來,他發現身體暖烘烘的,轉頭一看,姥姥一件被子都沒。這麼折騰,姥姥生病,他為了照顧又患上風寒,病得肌骨痠疼,央點零工的機會都沒了。幸好隔壁住的大娘看不下去,主動讓他們借宿,勉強熬過忽寒乍凍的夢魘。
這一病讓他在腦海悠轉許久的計劃決心付諸實現。聽村裡傳著替國家打仗不怕挨餓,又有實得薪餉。鄧文成聽了心動,他得替租來的屋子裝上門窗啊至少。
他虛報一年歲數,入了伍,並為了跟上軍隊,迎來匆匆告別的時刻。
他記得病還沒好全的姥姥開始蹲在厝邊唱著歌,他的姥姥一輩子養了那麼多人,可最終誰都沒覺得該養她。父母不詳的他被命運推向她,因為姥姥憐憫,從此相依為命。他雙手緊握著背包,在轉身的那刻卻說不出再見。
蹲在姥姥身畔,他輕聲說:「姥姥,我去去就回。您等我啊!」脣邊吐音輕得像一團棉花,留下很輕很輕的一絮,他凝視著,曉得姥姥無奈地答應了。無論如何就得賭這一把!他忖著一旦勝仗,向軍隊告假,立刻就將攢好的錢託誰給姥姥寄去。
起身,鄧文成腳邊揚起一圈粉塵,走了幾步,不意瞥見樹上停滿烏鴉。真不吉利,他想。一分心,耳尖捕捉到幾隻麻雀落地聚集的嘈雜聲,霎那間,樹上群鴉全飛了起來,朝著天空某處集翔而去。再轉頭瞥向姥姥所在的位置,卻沒見著姥姥。大概是進屋歇去了,他安慰自己。
破狹小屋進得可深了,這輩子,鄧文成沒能再見姥姥一眼。
一九四三年夏.中印邊境
他們把性命暫放在三十八師孫立人師長那兒。
不久前撤往印度之舉,令杜副司令長官怒極。鄧文成能感受到所有人都準備好賭上一切,跟著孫師長,行向燠熱的印度。至於杜副司令長官則帶著他的屬下捨命通過胡康河谷。
覆蓋血肉的皮膚細毛與衣料因汗水緊緊貼合,馬不停蹄以綁腿的雙腳行過崎嶇。一塊防雨的油布、罐頭和米袋、輕裝配備,水壺或毯子之類懸綁在土色背包上,兩兩距離一定步伐,隨時準備祭出手邊軍刀,或搏命以子彈應付任何危機。
在這,送命像齏碎一顆花生米,見血只是小事,一旦被恐懼抓住了,就沒有活命的機會。
他忍耐,傾盡全身來忍耐。
腦中還停留在前幾日孫師長站在戰車上,第一時間指揮向對方猛轟的身影。面對前方布署槍砲狙擊的日軍,子彈交鋒,雙方交火到昏天暗地,孫師長同時調度大批人力來移除路障。堅不可破的堵截防線眼看露出一隙,孫師長所在戰車的引擎噴出嗆咳黑煙,使勁全力,火速前進。在千鈞雜音之中,孫師長指令要所有將士緊隨突圍。
雙腿狂奔時,鄧文成聽見子彈火藥擦身的細聲。所有跟他同一時間蹬開腳步的同袍,以磨損破洞的鞋緊緊抓住地面,在毫無遮蔽的劇烈晃蕩下,迎向敵方子彈。
賭吧!不賭怎麼繼續?
賭盤一撤,孫師長引領他們在下個駐紮點休息。清點人數,犧牲的弟兄不多,但是每個人都曉得隔日,或隔日的隔日,陰險聰明的日本鬼子又將做好埋伏,等著襲擊。下回可能是空戰,靠著領空絕對優勢掃射他們預計前進的路徑,彈藥和血軀將會布及大地。
通往印度的過程僥倖不死者,都聞得出宛若源自腐土的死之氣息。生或死的機運各半,上天大手一揮,天平傾向某方,他或身邊的同袍就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葬命於這漫長而少有人煙的邊境之路。但就這樣了。拋棄已死弟兄,跟上急促前行軍隊的那一刻起,他就選擇了活著,活著繼續執行任務。
少年成為兵,他的心也成為兵器,剛硬如鐵。
報告,沒有敵軍!
快跟上。
踏進森巍巍密林,被指派殿後的自己跟軍犬一組,負責偵查隨時可能突擊的日軍第十八師團。
他全程警戒,寒毛直立,土生野獸般盡可能伺查任何天敵威脅。既要走得快跟得緊,剩餘的氣力為了不知多龐大的危險而預備著。無法交談,無法苦中作樂,第一次他感受到聲音憋屈在胸口,迴轉於肋骨間,把他推回那個心情慌張不定的告別。
姥姥知道他距離老家幾百公里,背棄了回家看她的諾言嗎?
只是,他的心被數不清的戰爭纏上了。作戰作為生存法則跟老家鄉間野狗交合沒兩樣,交纏密謀,齒間夾混尖刀來回刮動皮毛血肉的討饒聲,沒多久一窩崽子出現在樹蔭草叢,兩窩三窩,無端生了又生。野狗生存哪裡容易?可是不分晝夜幹上了,再怎麼樣都不可能消亡。戰爭也是,哪怕元首和元首互相握手,手心藏著準備給對方的禮物,交換禮物後不滿意,還能催生更多戰場,醞釀爆發下一波戰爭。說來,如同他這樣的小子離開貧窮村莊,想討口飯,賺點錢的,只有戰場等著他們。拿起槍砲,躲進壕溝,這種日子一旦開始,他才領會到沒有終結。反覆被翻攪、打亂、辜負的情況,不管是他對姥姥,抑或戰爭之於他。現在唯獨手臂包著繃帶,雙眼血紅的孫師長能夠信賴。
「今晚在這紮營。」前方發出停止行進的指令。
放下個人家當,從米袋中找出乾糧,吞到噎了,就努力生出口水。糧食也有軍犬一份,只是也不多。看得出牠累極倦極,而鄧文成通常寧可省自己的,也不願餓著牠。
休息,對於正在撤退的軍隊來說是不存在的,坐靠於背包旁,瞇一下酸澀雙眼,暫時不再狠狠盯著周遭,軍人跟軍犬都只專注想辦法在惡劣的處境中努力延續性命。
作為整支隊伍的殿後,得更放低生存感,逼自己直覺戒備到頂點。幸而後續仍有機會在下一秒安心下來,看著一隻無害的小型動物撥開草叢而去。那隨著緊張而大口呼吸的頻率慢慢緩和下來,過度換氣的肺部就此積存一股腐敗之氣。雖然如此,鄧文成就此生出一隻無名眼,聽力不知不覺馴得靈敏,窸窣摩擦,風吹草低,獸來過又消逝,什麼獸,或根本不是獸,而是必須起身反抗比獸更惡毒的敵人,這一切輔以軍犬的直覺辨別,曾幫他躲過幾次危難,還拯救了傷兵。
其實,自從得知路線無法繞過這座叢林,沒幾天,他的心臟總跳得非常急,因為呼吸不到新鮮空氣又必須疾行。近萬人豪賭性命,深入野獸埋伏,僅有各種毒物能存活之地,屢屢讓他擔憂老舊配槍要不得用來獵捕駭人巨獸,或斃死啃嚙他褲管下皮肉的蠍蛇。幸好,閃現腦海的懷疑總被孫師長神算般拯救。精準的軍事命令,奇技險招屢出,讓大夥躲過不少次殺人鬼族日軍的殘虐。
而正當隊伍即將通過隘口時,鄧文成的耳畔通過一絲不應該在森林出現的人聲。
他豎耳會神,是了,有人!
打出手勢,其他同袍即刻意會。他們列出突襲隊形,朝聲音源頭而去,攻擊當作防禦的瞬間,鄧文成不覺喊了一聲。
眼前還試著藏匿的是受傷的兵士,不是日軍。
孫師長很快親自下令沿途特別留意,收容掉隊或受傷的軍人,他們多是撤退不及的可憐人。為此,孫師長見了他。
走進臨時搭建的灰色呢帳,他第一次這麼近距離跟孫師長面對面。師長周遭都是三十八師的重要軍官,他們身著軍服圍坐,顯然在開會商討。
孫師長起身,面向他:「步兵,做得好。」
克難簡陋的作戰軍帳中,最尊敬的長官清楚看著他,並向他投以肯定眼神,其眼神恆毅如黑曜石,熠蘊堅實。鄧文成併攏雙腳,刷地舉手敬禮,孫師長以堅定的目光回看一眼,便又投入會議討論。
步出帳外,鄧文成瞥見天上新月,他逗留幾秒,朝更深處張望,整片天空充盈極壯麗的星海,一條履帶在群星中劃了條不可思議的光源,讓他猛然誤以為仰看著老家天空。這會兒,他深深凝視瀅燦的最大光度,恍惚從中得到一股意志,跟帳內的孫師長很像。
小心翼翼衡量生存條件,此次撤退依然很接近死亡。然而,他沒想過會有寧和安好的時刻。他也不會料到未來幾日,三十八師以極有效率的速度,持續護送沿途收容的傷患,挺進喜馬拉雅山麓。
省吃儉用的糧食差不多告罄的軍伍行進著,遮在頭頂的樹叢隨著高海拔而逐漸轉為瘦長拔高,前方弟兄泥濘血汙,毯子和頭盔在身上歪斜磕碰。太陽光直射威力讓長長的隊伍不時低首,無用但企求躲去毒日肆照。鄧文成揩了揩汗水,瀕近喜馬拉雅山麓並不能止歇汗腺,汗水或許源自未知的因素,於軍裝四處暈染汗漬。幸而他的聽覺在高處簌簌冷風仍十分管用,故能竭力區辨此地該有的及不該有的聲音。
繞進山坳,轉彎處有棵鳥群占據的枯樹。他悚然,以為是老家的烏鴉。突然,牠們清脆啾唱,在這麼高的群峰,音色陡然撞向山谷,一波一波。
忍住腳底水泡刺痛,他快步依然,而最前方傳來訊息—
到了,到了!
三十八師,不辱使命。鄧文成感覺步伐像是自有意識,晃蕩、狂馳。成功撤退到印度,不真實感遠勝於喜悅。
逃向生,就有人追向死。
與他們背道而馳,向北撤回雲南的第五軍,就在他們終於安穩駐紮在印度阿薩姆邦小鎮利多之後,傳出毗鄰利多的野人山那兒有他們的足跡,連當地人也畏懼不已的極惡之地。這支應該往北走的師團,竟成為他們接應救援的對象。出現在眼前的第五軍和二十二師的劫餘者,軍服髒汙斑駁,露出的皮膚斑駁著新舊傷痕。遠遠地,身上瀰散的氣味讓鄧文成跟左右袍澤深深驚駭。
—他們已經不能算是軍人,而是帶著濃厚病氣的失魂者。
僅說僥倖從野人山逃出,除此之外,他們什麼都不肯說,喉吞硬石,眼神壓低。接近而遞出水跟食物的瞬間,鄧文成不意聽見了。
有可能嗎?恐懼會有聲響。
周身細微顫抖不輟,被什麼擊中或通電似的,不停延宕著後續的顫動。
懷著只有自己知曉的驚懼暗影,與大夥一起招呼逃過大難的他們吃更多的飯,雖說飯也不過是粗糠。入夜,圍著篝火飲烈酒,熱辣得不明所以。映照中,隨著火光無限延長的影子時而張牙狂笑,時而扭曲縮小濃重墨黑到闃冷。坐在溫暖而安全的異域土地上,撲簌簌地有人抽泣起來,顛抖的肩膀胸膛使得還未從戰爭中清醒過來的人,疊加嚎哭。哭聲放大所有外在音聲和動作,經烘乾龜裂的樹枝柴木一遭火舌吞舔,下一秒是大規模的燃燒,一場不可逆轉的局勢。
這些臉孔遭遇所有泯滅人性的事,哭聲不似普通人,沒有人能持續一整夜的悲泣直到隔日。
「多少人?」漫漫長夜,有人終於問了。
鄧文成醒來,一雙銳耳喚他從夢境起身。
數字化為火星沫子,風一吹,一道纏繞交疊壓迫感的枝椏,暗影祕密隱匿著身形不明的野生動物,雨一場接力一場,形成洪流,忽遠忽近的腳步聲伴隨瀕臨作嘔的氣味,活迸迸的鮮血蝕爛的屍體死壞的斷軀橫陳的馬首舉起毒螫在等待的蠍子,忽地迫近一連串大炮悶響,踐踏聲響,大地震動,悲鳴咳血般的慘叫聲直通天際。
鄧文成睜大眼睛,像是從水底深處忽然被拉回陸地,瞬間又被不明的大火灼傷,他的耳朵不曾關閉,握緊拳頭直到筋骨痛麻。
一年後的十月,新三十八師打通野人山,鄧文成一如最初那般追隨孫師長,成為潰擊日軍,獲得大捷的萬人功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