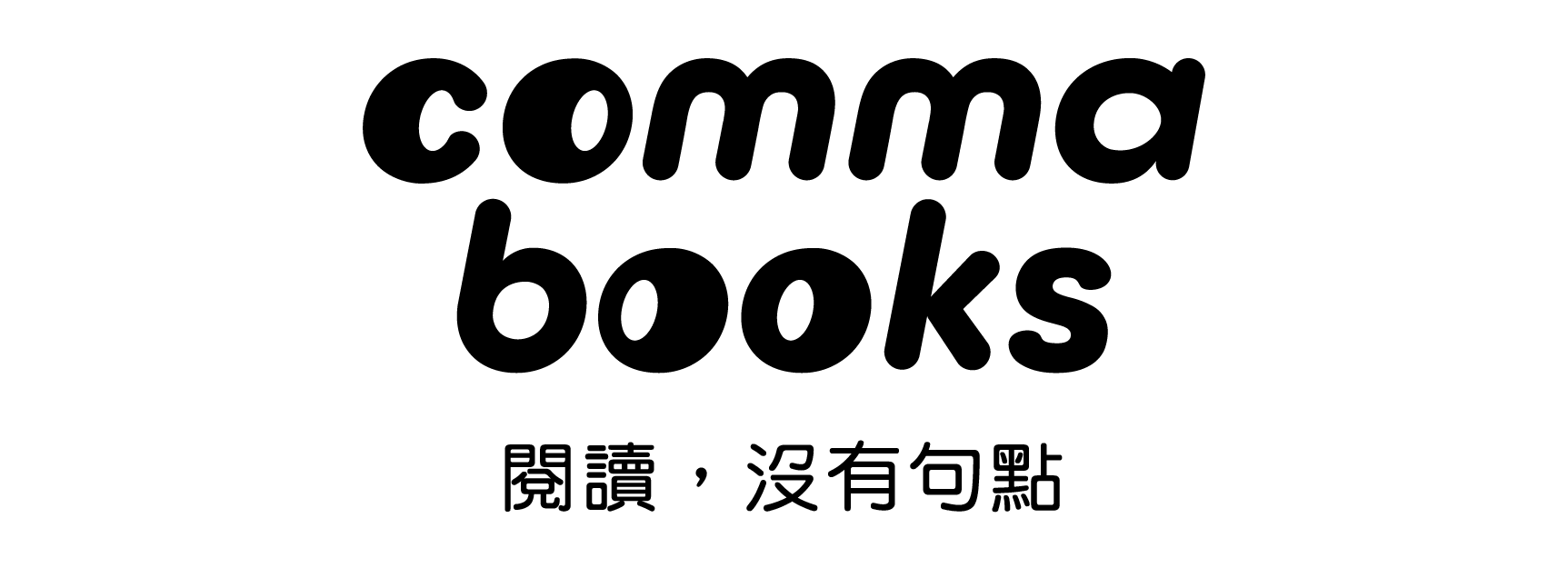陳育萱《南方從來不下雪》〈放生〉(下)
二零一九年秋.高雄
「小寶,你說說,我這是醉糊塗了嗎?」小寶趴在人行道,眼皮微垂,嘴間咕噥一聲算是回答了他。這兒的人行道插滿國旗,今年雙十國慶直到現在都還未卸除。
青天白日滿地紅,他也曾被拉去造勢現場,上千張塑膠椅上放著國旗,穿著國旗裝的老方興奮地向他揮動國旗。鄧文成接過一支,臺上很快開始拿著麥克風喊話,鼓譟臺下一起。
國旗,從軍的他怎會陌生?他拿著,眼角餘光望向老方,老方身後還有一群再一群,無盡湧入的人潮,各年紀都有。除了人潮,會場外圍是車陣,汽車後方綁著疊高的國旗旗竿,機車騎士不少戴著國旗安全帽,也綁著國旗,所有人極盡可能地舞動旗幟,那股興奮聲浪使他懷念起跟當年同袍追隨孫立人師長來到臺灣時,每年村子裡的旗海飄揚,尤其熱烈地展現對國家的忠誠。
自從村子改了名,出了事,他曉得自己再也無法那麼熱切地揮舞國旗了。
欲說還止的紛雜心事也包含小寶。
鄧文成索性坐在欄杆旁的基座上,盯著小寶看。牠十五歲剛過,患有輕微腎臟病的牠,需要打針吃藥,可是醫生說牠還算健康,不用太煩惱。現在的自己跟小寶都是垂老病多,特別是近日,他感到尤其吃力。
小寶來的時機,孩子們已經都上了大學,隔坪不怎麼方正的屋子偌空起來,邊角縫隙也開始有了壁癌。小寶剛被發現不過田鼠大小,妻子掛上老花眼鏡,從草叢堆中主動抱起牠,為牠準備牛奶,看著還是嬰兒的牠狼吞虎嚥。
自從有妻子餵養,長得很快的小寶活躍起來,不久便嘗試要走路;遇到門前階梯時不小心滾落在地,筱惠的笑聲就從窗臺傳來。妻子抱起小寶,像是要帶牠認識新家,指認家中擺設,植物,用手觸摸著屋子壞朽的部分。鄧文成隔天拿了工具,準備重新清理與粉刷。
與他一起逐漸老去的妻子已經不太做貼補家用的精細手工了,她偶爾去找牌搭子,要不就是占據他的藤椅,在屋子裡看看書。鄧文成也是很後來才意識到她喜歡書。這些發現,讓他格外仔細整修屋子,從內到外,包含老朽的窗框和書架。
他簡直上癮了。這棟屋子竟然有這麼多地方該翻修,之前怎都沒發現呢?
更換、整修讓鄧宅重現勃勃生機,鄧文成、妻子與小寶,輪番散步,洗大小瓢盆,取出原來早被白蟻蛀光的木椅,把窗戶拆下以水柱噴洗。勞動的時間特別會感受到陽光,晒著衣服的庭院空地暖洋洋的,後頸、腋下和後背全都汗津津。
這之後,妻子便會悉心準備晚餐,雖然只有他們倆人,她仍願意耗時烹飪。時不時出現的豐盛大菜,像是酸菜白肉鍋—
好吃,味道太對了!
鄧文成不自覺誇出聲,讚嘆迴盪在神情渙散的小寶身周,他才察覺牠半寐沉睡了。之前住村子裡,牠有多活潑啊!跑遍全村也不喘。為了不吵醒小寶,他把項圈栓在圓柱狀的石柱上,打算去旁邊的攤商隨便買份食物。
他知道自己依然下不了決心。
本來,他想將小寶不經意地放在妻子舊家,讓妻子的親戚自然而然地發現這隻狗。可是,每當想起鄰近妻子舊家的路,他亦手心發冷。妻子病逝後的那幾年,他必須耗一整天在外浪走,返回眷村老家才睡得著。
多事之秋的村子對他來說不再是堡壘。
暫且甩開這些念頭,他向賣蚵仔煎的小販買了一份,想了想,又點了隔壁攤的海鮮粥,囑咐說不要加鹽。現在的他,應該比老妻更喜歡海鮮了。他甚至特意張望左右,看看有沒有哪家攤販賣烏魚子。
「你知道……我現在……最想吃什麼嗎?」病榻上的筱惠抵抗虛弱,這麼問道。
鄧文成看著插著鼻胃管和其他數不清管子的她。他始終都握著一條白底紗質的繡花手帕替老妻擦眼睛,她的雙眼因為久病而混濁,過去的她可有一雙愛笑而晶亮的眼睛哪!
「浸過高粱,火爐上剛烤好的烏魚子。」她說的話一字一句非常輕緩,呼吸聲濃重。
孩子們都趕回來了,只是沒有一個人走出病房大門去張羅這項食物,他們擔心的不是媽媽想吃的,而是媽媽的性命。
醫師低聲宣布,這一關過不了。
一刻之間,兒子立仁、立德,女兒如燕、如鵑全擠近床沿,想跟全身浮腫,眼神慢慢無法對焦的妻子道別。某個時間點走進來的醫師,關掉儀器。鄧文成聽見儀器停止運作之後,始終待在白色空間內的筱惠,發出咑的一下,極輕極輕的挪移,脫卸了肉身。
醫師在場宣判死亡時間後,一旁的護士開始把管線慢慢收回,他們的動作好像剛完成了一場大型活動,現在拔除電源。
一切都結束了。
離開妻子故去的病院後,為了後續的喪葬事宜,鄧文成接受二兒子立德的好意,到他們家去住個幾天。
坐進休旅車內的每個人全不作聲,負責駕駛的二兒子向前疾駛,掠過一個又一個分隔島。鄧文成覺得四個輪子抓不牢地面,在一顆顆綠燈催促下,宛若飛昇了起來,唯獨心臟很沉很硬,血流跟身體相互背離。
鄧文成下車,準備踏進二兒子在北部郊區的別墅前,大兒子喚住他。「爸,以後來我家住吧!」特地從美國趕回來的立仁,經多年努力,已是美國執業律師。鄧文成打算後續殘年跟小寶相依為命,但他選擇向大兒子點頭,「知道了。」
只是……他內心默點著送別後,哪個女兒就率先說要回家一趟,而誰家孩子吵著要吃肯德基。他奇怪著沒人提議要全家人聚一聚?還是,大家真的這麼忙?
回想四個孩子自從那件事後,他們之間就少說話了。鄧文成並不後悔,當時,他得保護這些孩子和這個家。
說來是那個下午太過突然了,下了班的返家途中,他被攔下。對方向他自我介紹,出示官階姓名,之後便為他蒙面,逕自帶走他。
在那個房間裡,負責談話的人跟他對坐在亮晃的方桌前,對方問什麼,他就答什麼。
他說過自己好像看過誰出入過郭廷亮的家,名字不記得,只曉得長相。對方一旁有站立者,刷刷記著他所說的一切。問話的人,語氣懇切,鼓勵他說更多些。
這樣是不是孫師長就能復職?
對方向他露出微笑,而他在這抹表情裡得到首肯的力量。他知曉既然要說,就得交代得越清楚越好,知無不言,將他所曾記憶的,具體描述給對方。
聽著他闡述時,對方總是維持著澈底的沉默,而或許因為沉默,那張與他對視的臉,後來竟想不出真切的輪廓。鄧文成感覺那是白的,消融五官的白。
從那單位離開的時候,他明確收到了交代,「請不要透露任何事,鄧少校。」
他點點頭,讓他們用一樣的方式放他回到平常的路線上。返家途中,他還盤算好幾個理由跟妻子說今日的遲歸。
推開紅色鐵門,他貌似聽見妻子向孩子說幾句,而孩子頂嘴的情況。
「幹什麼東西,敢這樣對你媽說話?」鄧文成箭步上前,給立德一掌。
身為哥哥的立仁,竟然把弟弟拉到身後,向他怒目以對。過去擔任潤滑劑的兩個女兒如燕與如鵑並不在家,家中就是這兩個血氣方剛的兒子。
鄧文成把立德拉拽出來,斥問他的無禮。他大概猜想得到妻子教誨兒子的內容,二兒子在校老是闖禍,一定是老師還是教官又打電話來了。基於這個方向的猜想,方才被請到其他地方問話所積累的不安,沒來由地點燃他的怒意。迸升的怒火,交雜著他一時也說不清的,對於兒子們行為不當可能引致的不幸後果,他隨手拿了東西,朝立德跟立仁身上招呼。他的力氣縱然不比當年,舔拭並加劇火勢的外在因素,一切都能合理燃燒。
妻子在旁勸阻,根本壓制不了。
直到她嘶聲一喊,將煮好的湯揮到地上後,鄧文成才愣住停下。兒子們見狀,找到機會也怒氣橫生地闖出門,整個家只剩地面一片狼藉。妻子的表情泫然欲泣,而她的腳背竟紅腫一小片。他拿了抹布想擦,可是妻子卻推了他一下。他再次伸手,妻子卻更用力地推他。
「你幹什麼?你幹什麼!」妻子對著他,「都是你……」
令他驚怖的三個字,都是你。
無數夜裡拷問自己的,再度使鄧文成無語。他到廚房去拿冰塊,妻子斷續說著兒子因匪諜二字,在校跟人衝突的事。
這該怎麼辦?不如我買一盒水果,去跟教官還有同學道歉?
這根本不合理,也不應該這樣。媽,好了,妳別管!
話鋒截斷在此,是他將衝突複製到家裡,鄧文成感到懊悔,可是他分不清究竟是哪一件事更為後悔。
大概因為這樣,兒子跟女兒們,漸漸與自己疏離了吧?
毫不相干的回憶,遺憾的時刻,他也想起遙遠的歲月的某一年,他向姥姥承諾的去去就回。而今妻子先去了天上,反倒是她先跟姥姥見面。不過,她們一定還互相不認識,等著他,等著他去會合……。
他甩甩頭,他得照顧小寶啊!小寶總趴在門前守著,牠很會認人,又常常一張臉那麼開心,村裡的誰牠見過一面,之後再訪,牠是第一個衝去迎接的。
妻子抱來養的小寶,他得讓牠好好的。
後事辦妥之後,鄧文成回到一人一狗的家,努力維持跟往常一樣的生活—照常遛狗,照常依照妻子囑咐的,煮三餐給自己吃,偶爾跟鄰居閒談嗑瓜子下棋。
越來越少戶人家明亮著燈火,住在這個村的人漸漸地歸於塵土,活著的,有好幾個想存老本卻投資失敗,不知去哪了;少數跟兒女搬去寸土寸金的豪宅,邀過他去作客。
他以為自己會在此老死,躺平在床上,等到屍身腐爛後,這村子裡剩下的好弟兄會通知兒子女兒們妥善埋葬他。連後事都想好的情況下,某日竟毫無緣由地接到政府一紙通知,公文上說要重建這眷村,因此所有住戶都得搬遷。他們可以選擇領賠償金或是住進國宅大廈,二擇一,沒有更多。
那陣子家中來電特別多,有些早隨子女遷居海外的,有些是村裡與他一般苟存一口氣的。
怎麼辦?政府怎麼可以這樣?
操他奶奶的,來組自救會啦!
我打算領賠償金,就近搬去我兒子媳婦那。
七嘴八舌的訴苦、出主意,總歸是慌張有之,遭背叛的氣憤占據了電話線路,他握著話筒聽得太多,簡直快耳鳴!難道不曉得他的耳朵大不如前了?
小寶看著他,在話筒旁嗚嗚發出要散步的提醒。
「好了!別說了!」他終於忍不住那人又乾又扁的聲線,絮聒如老鄉群鴉。
認為應該站在同一陣線的對方,大概沒想過鄧文成有這反應,在另一端愣住了。
掛斷電話後,鄧文成舒了一口氣,隨後為小寶繫上狗鏈,小寶樂極,開始轉圈踢跳。他跟小寶走進村子裡的小學,又繞進每條巷弄,由於跟往常的路線不同,小寶幾度抬頭望著他。
他只輕輕向小寶說:「來吧!以後我們就不走這兒了。」
小寶動作輕快活潑,這樣的時機下,他凝視著挺拔俊俏的小寶啊,忍不住停下抱住,任牠舔著自己的臉頰。牠取代了某道身影,連妻子也不曾告訴的,某道救贖復活於他的心底。
回到人行道,鄧文成拎了熱騰騰的食物,可拴著小寶的石柱空無一物。
小寶?他環顧四周,海邊的人潮少了許多。
他吹起口哨,哨音又長又響,這是呼喚牠來吃飯的訊號。
毫無回應的情況下,鄧文成焦慮後悔,加上沒帶老花眼鏡出門,現在又該從何找起?牠年紀不小了,應該沒有人會拐走一隻老狗才對。他安慰自己,可越走越遠,浮現的假設越偏焦慮。
—會不會牠醒來沒看到我,自個兒跑回家了?這趟公車這麼遠,現在的新家老早就不是有著廣大樹蔭的村子了,牠鐵定迷路!如果迷了路,天色這麼黑,誰會注意到牠?牠不太吠的,該不會被車子撞上了?
鄧文成年紀使然,沒辦法走得快,旁人看他大概正在海邊悠閒散步,卻無人知曉他的內心焦狂不已。他考慮如果回程再沒看到牠,就先去警察局備案。這麼決定之後,鄧文成的步履暫時踏實多了。然而,直到他回到原處,又到公車處繞了一圈,依然沒見到小寶蹤跡。手中提的食物老早涼了,他完全沒心情吃。他問了當地居民警察局的位置,又花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警察局。
相較於軍人,他對警察還算有好感。之前新建大樓內有住戶鬧一整晚,他撥打電話至警察局,員警沒多久就趕過來處理。這次,他主動地進了警局,坐在最前方的警察正在吃晚餐。
「請問這位警察先生,可以接受報案嗎?」
聽到要報案,警察抬起頭來問:「什麼事件?」那是一位戴著黑框眼鏡年輕的警察,而另一圓墩墩的中年警察則起身站到櫃檯邊。兩位謹慎的態度頓時使他歉疚地記起這趟是棄養小寶之行。
他猶豫應該怎麼說,說什麼?不一會兒入神,勾住食物的手指不小心鬆開,灑出滿地湯飯。溢出的食物氣味引起所有人注意力……。
能住或不能住,能活不能活,一道指令或一紙命令,決定了人生去向。
發出拆遷公告後的幾個月內,經自救會陳情、抗議、斡旋,居民們還是只能依循安排遷移到新建大樓裡。大樓內除了他們村,亦有其他因都更入住的住戶。
從平面搬遷到立體,站在頂樓的鄧文成對於只能低頭看地面車燈殘影感到不可思議。平日見不到鄰居的公寓雖然新,住起來卻很麻煩。過去只要踏出家門,巷口便有不同族群能夠聊天,現在是他得拿著一張備忘,一一記著哪一層哪一戶是誰,才搭電梯去按電鈴。
電鈴多按幾次,旁邊的鐵門就忽然開啟,不認識的臉孔透過紗窗不耐煩地出聲:「要按多少次啦?吵死了。」被這麼不識相的嗆聲幾次,鄧文成的興致大減,索性繭居在家。
起碼還有小寶,他想。然而,不只他住得不慣,小寶也是。剛搬進來那天,小寶數度掙脫頸繩,向門外衝。他費好大工夫,才讓小寶跟家當一起住進。
小寶喜歡跟他一起串門子,自從他住進這地方後,不曉得怎麼少了動力帶牠出門。他看著窗外,好天氣時依稀能見到村子另一邊的圍牆。
牆內世界荒誕依舊。聽聞出獄後的郭廷亮不慎跌下月臺死了,他幾乎忘了同村郭廷亮的臉,其實也從未記得住曾約見他的情報單位人員。現實的世界則是孫將軍長期被軟禁在臺中,十多年前仙逝。
人假若不須交換條件,人可以活成什麼樣兒?
近一個月來,半夜聽到好幾次門鈴響或接到無聲電話,張貼於大門的警告紙條以紅筆寫「不准養狗,否則不得好死」。撕下這張威脅時,鄧文成不曉得對方是要他不得好死,還是要小寶的命?或者兩者都是?這張出現不只一次,他沒向兒女說,亦未向他們提出送養小寶的要求。
說來,他帶小寶到老妻的故鄉,另一種想法只是想藉由命運的偶然,撞出一點機會,說不定牠會遇見一個好人家,如他當年。如此,牠就不必跟著他住不喜愛的公寓,還時時受威脅了。
曾經,小寶四肢健全,尾巴完好,渾身短而閃亮的毛,正值青壯的小寶多引人注目,可惜老了之後鬍鬚下垂,嘴邊出現星點花白,變成一隻好平常的黑狗。即便這些平常,對他來說非常重要,非常特別。
如果要描述小寶,他會描述咬下一枝七里香,像個頑皮孩子在村中繞圈的模樣嗎?抑或只輕聲呼喚牠的名字,牠就會立刻蹲坐下來,伸出手的習慣?
鄧文成瞪大眼睛看著員警,員警要他慢慢講。
意識帶著他回到某個瞬間。
叢林內一批衣服破損髒汙的人,其眼神冷靜兇狠,渾身負傷流血。他判斷對方只剩短刃,準備衝上一搏時,日本軍竟然狡黠地變出一把槍。那瞬間,隊上唯一的軍犬迅雷衝上前去——在異邦神靈的默許下,牠成為子彈的犧牲者。為了他們而死的犬,腹部流出大量鮮血。憤怒激引他們使出自己都料想不到的迅速追擊,殲滅了敵軍。
犧牲的軍犬,鄧文成一度堅持抱著牠前行。
「今天晚餐吃狗肉。」最前方傳來的命令源於隊上糧食告罄。
「嗯。」他至終都後悔那一刻的服從。這是他參與訓練的第一隻,也是唯一一隻軍犬。他當初向上級保證牠對這趟遠征很有幫助,真的。
牠救了他兩次,一次是替死,一次是成為他的血肉。
把牠養回來,重新給牠新的名字,牠是小寶。
嘿嘿嘿,牠就是小寶——牠的孿生兄弟可是建了軍功的你們知不知道?
鄧文成跪地長笑,自己怎會想犯孽放生牠?他直敲著地板,直到手都沾滿了冷腥的海鮮湯汁。
某年.除夕
「爸,你醒了?」
聲音帶進一位身形瘦削,方形下巴,穿著格子襯衫和棕色大衣的男子,他看起來有點疲憊,不過聲音飽滿宏亮。
「我知道你住這裡一定很悶,所以我把Nico帶過來了。她剛從學校放學,你看,她今天的打扮。」
「爺爺,你看看我!」女孩甩動馬尾的樣子輕盈可愛,她的臉上有著迷人小酒窩,長睫毛快速上下扇動,嬌俏模樣讓人挪不開視線,直在心頭滑起輕快音符。
她在床邊伸展雙手,踮起腳尖輕輕挪移粉色薄紗篷篷裙,模樣自信又陶醉,好一隻優雅的白鷺鷥。
門在這時推開了,一位穿著護士服的金髮女子推著一車物品走進來,她的身型巨大但微笑溫柔,一進門就跟那位方臉男子交頭接耳。而那叫Nico的小女孩飛撲到床邊,仰起煥發著光亮而近乎透明色澤的臉,帶有寶藍紋路的眼珠好奇地上下掃視。
短短片刻,直教人心生憐愛。至少自己忍不住想摸摸她的頭了。
這念頭才剛冒出,他便摸了摸她。她誇張地張嘴笑了,瞥頭說:「爹地,爺爺好像認得我。」
男子對女孩比了一個讚,隨後匆匆結束另一場對話。
「爸,現在身體會不會不舒服?護士說目前還在觀察期,如果之後沒什麼問題的話,就可以轉到之前你住習慣的房間裡。」男子說到一半,有點遲疑,「還認得我吧,爸?前幾天你怎麼了?護士說你發了好大一頓脾氣,翻倒食物,又把房間裡所有東西砸爛了……」
「我是你兒子立仁,這是你的孫女Nico。你什麼都不用擔心,好好休息養病。」男子伸手覆上他的手說道。此舉讓他留意到自己充滿皺紋與斑點的手,青筋糾結的皮膚在空氣中有一絲乾澀緊繃。他們臨走時,他向準備離去的男人和小女孩舉了一下手臂,不曉得這樣夠禮貌沒?
無人打擾,他躺下。
四周是澈底的白,白色的窗簾,浴室白色的門,門後的洗手臺與馬桶也是白色的,他的床,枕頭,棉被都是。
天花板的白被他盯得久了,他便從中看出一點不同。
光潔的白,慢慢出現了層次,像是有物體特別要教他發現一樣,開始產生了陰影。陰影的濃度最初都是淡薄的灰,細瞧著,便有鼠灰色、柏油色逐漸顯影。隨著陰影游移,畫面躍入,有一顆手榴彈朝自己扔來,他的眼角餘光見到有人以槍托揮桿敲擊,在他都來不及別開眼的時刻,產生了爆破。他雙手遮頭,讓自己重重摔進腐爛的植物裡尋求庇護。酸朽的氣味被嗆鼻的煙硝味入侵,他所能感受的空氣瀰漫著極其噁心的味道。
再一眨眼,他眼前出現炒臘肉盤、鮮蝦元寶,一盤盤誘發熟悉感的菜餚在他眼前羅列,冒著白煙的是酸菜白肉鍋特有的酸香氣,肉片和蔬菜在滾湯中不停躁動。有人率先動作—
「爸,敬您。」
聲音像是附耳在旁說的,而高舉戧彩白瓷小酒杯的是剛才帶著可愛女孩的方臉男子,還有好幾位與之神似的男男女女,年幼青壯均神情愉悅,搞得他也不忍心掃興了。
「好,乾杯。」
簡潔有力的回答宛若點睛,一下子讓桌席熱鬧活絡起來,紛紛停下手邊事,朝他舉起精緻小巧的杯子,手伸得老長,直到杯子親密相碰—爸,新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