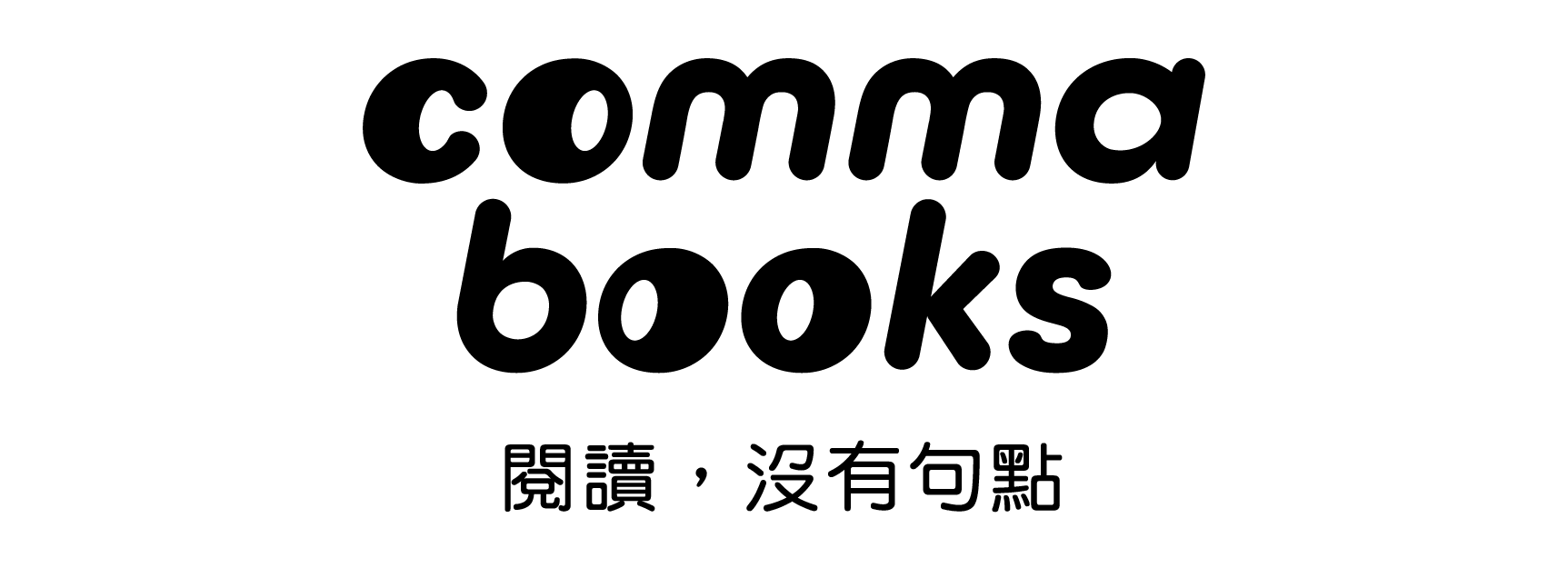陳育萱《南方從來不下雪》〈放生〉(中)
一九五四年秋.高雄
磚房紅門,巷弄互對,巨木遮蔭下靜立一排日式宿舍,透出寧靜。
村子旁的小學是最初將軍為了照顧軍隊部下後代所興辦的,於是村子裡的孩子幾乎就在眼皮底下讀書。外人進村,得先行經全臺最大的牌坊,由水泥柱與鐵條框住幾個醒目大字「誠正新村」,而鄧文成也位居其中一戶。
幾年前隨將軍渡海,抵臺後他們輾轉被安排住進這區日軍遺留宿舍,對面是將軍主導的陸軍訓練基地。初來臺灣的他,海島溼潤的空氣,焰火般的日頭,南洋風情的行道樹,很容易疊合二十初頭深入滇緬,駐守印度操兵訓練的印象。遠離印度藍姆伽整訓時期,成功撤離緬甸戰場後,他們與將軍之間的聯繫便少了許多。不過訓練一事仍是將軍念茲在茲,持續操練的事。
從戰場歸來是當時十六歲少年的心願。不打仗後,總算過上不須驚惶的日子,鄧文成內心寬慰。
工餘返家後,通常他會選擇坐在客廳裡,敞開窗子,坐在躺椅上。而狹小院子的竹竿一排乾淨衣褲,在風紋絲絲擾動之下,散發淡淡的水晶肥皂味,似遠若近的人聲嬉鬧,饋予平靜。物什還算堪用的家,妻子收拾得乾淨齊整。不少戶人家批來手製品,加工賺零花,唯獨妻子與這個家最是有條不紊。
出身茄萣的妻子,自幼習慣與海共生共處。
輾轉於內陸作戰至移居臺灣,對於這座島嶼上的風俗與習性,實在說不上習慣。
畢竟他跟弟兄們都深信誓言不久後要帶他們攻回去的領袖。獨來獨往如他,什麼也不怕,領袖說要走,他隨時可以。帶他們來臺的領袖不會誆人,他深信著。
因而,某日當局宣布同意他們在臺娶妻生子時,一抹錯亂使他遲疑軟弱。
這背後昭示的喪家感,讓他終而下定決心。
那天,渾身壯碩的鄧文成穿上版型挺亮的新製西裝,仔細梳妥頭髮,帶了聘金聘禮,前往海邊人家提親。這副打扮的確在女方左右鄰家引起一陣騷動,年紀大女方十歲的鄧文成提親成功,如願娶回依海而生的妻子筱惠。
筱惠比他想的還更適應住進眷村的新生活。聽她說,之前想種的花草屢種夭折,她被家人笑稱憨慢,現在住在海風吹蝕不到的地方,她種什麼是什麼,七里香和桂花從矮叢就屹立在圍牆邊。儘管別戶人家盡是色彩妖豔的扶桑花,他們家長年綠意一片,節氣到了才點綴一些淡米色小花。
「摘完的桂花,要拿來泡鹽水。」女兒們捧來鹽水,盯著細碎如金的桂花在水盆中,逐漸面露驚訝,水的表面出現細小的蟲,在之中載浮載沉。她們以為篩網留下最飽滿的花蕊便大功告成,卻意外在之中見到一隻隻被水逼出的蟲。
「好噁心。」大女兒如燕忍不住叫道。
「我們喝桂花蜂蜜的香氣都是從蟲那邊搶來的。」妻子淡淡地說,順手將幾隻明顯在求生的蟲輾死。
女兒們愣愣地看著妻子,不多久,女兒們就習慣了凝視蟲子的死亡。
他在半敞開的門簾旁看報紙,兒子們漫不經心地剪著妻子吩咐的香椿葉,好讓妻子做香椿餅。但他們又不肯好好做,趁空猜拳,輸的人負責出來剪,其他兩人偷偷蹲在一旁玩玻璃彈珠。輸的人動作粗魯,連細枝都折了下來,只一心想搶回彈珠。
鄧文成想以一家之主的身分喝止他們,轉念尋思,二女二男,各自有小樂趣有什麼不好?
目前他的樂趣是看報,下棋,跟村內的昔日同袍話當年。這麼一想,又將報紙掀往下一頁。他沒料想過,不久之後他將在報紙上見到使人驚詫的匪諜二字,與自己引以為傲的村名並列。
一九五五年春.高雄
小滿剛過,稻田抽穗黃熟,吹到身上的風隱約是夏的氣味。
妻子筱惠在廚房滷製的香氣飄出,下鍋麵條正滾燙著。撈起放涼,澆淋豬油,再舀幾塊豆干,灑蔥花,這是孩子們的最愛。
「吃飯了。」
戶戶相連的村子,喊著吃飯的聲音很容易互通,誰負責端菜,誰得去巷口把人叫回來,各如栽植在各院不同品種的花,簇擁堆積,圓滿地在耳畔開綻。
不用特別優異的聽力,好的壞的在這兒什麼都聽得見。
這一日傍晚時分,幾輛軍用吉普車駛進東二巷,一陣粗聲吆喝自巷口傳來。
聽聞不對勁,鄧文成要孩子們安靜。
「誰是郭廷亮?」
器械鏗鏘聲響,引起驚呼,左右鄰居多少見過郭廷亮軍訓班同學高培賓。高培賓被粗魯地扯向一旁,而郭廷亮竟雙手被銬。
其他住戶渾然不知是什麼事,基於義憤,議論鼓譟起來。幾個熱血兄弟衝上前去,想澄清辯駁,反遭站在最前方的憲兵搶白:「誰替他說一個字,誰就有匪諜嫌疑。」不一會兒,荷槍人牆鞏固在屋外,不准任何人進入。指揮的軍官順手一揮,下士魚貫湧入,對著牆壁、櫥櫃、天花板又敲又戳,粗暴地發出讓人心寒的噪音。這場面鄧文成窺看著,眼見身著軍裝的那群顯露出非得要挖出什麼的凶狠神態,不禁脊背發涼。
憑什麼押人?
鄧文成屢屢難忍,直想推窗大聲質問那群前來搜查的軍人。他們的長官是誰?不明不白抓人,使他多年來止步於征戰場合的片段記憶逐漸復甦。
他轉向另一角度,望向押坐在車內,沉默無語的郭廷亮。
莫非……
一瞬間鄧文成腦中浮現不妙的念頭,又旋即為卑劣的想法而懺悔。他接連低聲辯駁不可能,好像持誦咒語般,足以抵銷口業。那番搜索很快了結,抓人軍團迅速上車,加速揚長而去。在車輪快速馳過村子時,樹上提早的蟬聲零落地,間歇地,鳴放了幾聲。
自那時起,懸在村子入口,帶有品德深意與期許的定名,替換為毫無關係的稱呼。
村子開始壟罩在一種安靜之中,此非尋常安靜,而是預防即將發生什麼而刻意保持的安靜。同樣位在東二巷的住戶們,包含鄧文成一家,靜默流轉的猜想從扭斷言語溢出,無時不刻;人們只要路過,都特別留意是不是又來了一輛軍用車。
報紙上刊載,政府已確證郭廷亮為「匪諜」,而其長官孫立人「縱容部屬武裝叛亂,窩藏共匪,密謀犯上」,數項鑿鑿罪證印為鉛字,孫立人將軍確定革職。
親自見到這樣的消息,鄧文成闔上報紙,重重一聲,一列骨牌在他心底傾倒。
村內昔日跟著孫師長作戰的弟兄們才霍然察覺到一隻隱藏在這個小世界之外的手,摸黑取走了很多戶人家的燈。再平常不過的矮垣,龍眼樹下的幾張空藤椅,鄧文成開始偶爾恍惚錯認是他們萬人反攻緬甸過程中,必須機警懷疑的日軍陷阱。幾個弟兄在他不知道的深夜,無緣無故失蹤,被抓捕的原因繪聲繪影,他們彷彿被詭異的藤蔓纏住了,懸到半空中,讓其他行進的同袍毫無所覺。
鄧文成再不看報紙了,上頭所寫的全是不讓人爽快的消息。
「你若有一天不在怎麼辦?」筱惠有次在熄燈的床頭邊問道。
「別胡思亂想。」鄧文成拒絕想像,內心滿溢不可名狀的憤怒。
「不是……我聽隔壁巷子的……」飄忽的話欲言又止。
家裡四個孩子睡在隔壁的通鋪,他的心因為高頻率的憂惱而厭鈍,一旁背對著他的妻子等不到答案,應該是睡著了罷?他關上眼皮,意識還飄移在半空中,又是一個不眠的夜。當無法安睡的日子逐漸堆疊至高時,他的身軀便不再如以往那般敏捷了。他開始偶爾會在上班時間打盹,說話也不似之前宏亮。少年時代出生入死,毫無所懼的氣力,不知怎地從一根一根的手指尖滑開。
為了振作精神,暫時隔離內心的躁狂,他叫來兒子們一起慢跑。在村子旁的國小,繞著操場一圈又一圈跑著。他賣力回想過去操練軍隊的情況,大喊:一二、一二,並要求上高中的兒子們一起喊出聲來。
兒子跑完前三天,就蹺了他的跑步訓練課。
晚餐桌上,他為了這事特別要兒子們拿出成效來,不然愧為學生。最先他不是要提這個的,跑步的好處他都還沒說上一個字,剛上國一的立德低著頭,把一碗飯的米一粒一粒撥進嘴裡。見狀,鄧文成怒氣張揚烈焰起來。他很少真動怒的,然而那次卻被怒氣帶著亂竄,直到那把火掃得餐桌上人人速速掃光碗內食物就離席。
很久沒來串門子的老方,正巧敲了門,他手裡拿著高粱。兩人對坐,那雙多毛而巨大的手,持起玻璃小酒杯敬他。喝了幾杯後的鄧文成,喉嚨灼燙。他曉得老方是有辦法的人,軍階比他高,又跟上頭關係好。
「你知道咱們村裡那些人都去哪了?」鄧文成啞著嗓子開了話題。
「誰知道?」老方斟滿酒,他的眼瞳閃爍一抹喝止。
拿起酒杯一飲而盡,才幾杯,好酒量的鄧文成竟感覺有些頭暈,喃喃道,你知道吧,你知道。他半是藉酒胡鬧,半是太久沒這麼喝了。
他的腦中冒出一個泡沫般的畫面,有人從身旁中彈倒下,倒下的背影不顧一切。他朝左右大吼,小心—然而,更多轟然的爆破聲踩住他的咽喉,他的警告幾乎連自己也救不了。他舉起槍,瞄準,婆娑樹影和詭異影廓都成為他的目標。扣下板機,趴下—他要給那群日本鬼子好看。抽動的直覺讓他擱下槍桿子的瞬間,聽見連長對他大叫。叫的聲音不像平時那麼兇,而是一道尖細的錐子刺進太陽穴,從腦子裡發出聲音。
快讓鄧文成停下來。
其他人讓他伏低,臥倒,接著無數隻手抓緊他全身上下。
夜鴞從樹層之間飛過,比人膝蓋還高的草叢跳出一隻蜥蜴,成為一個點,緊接著渾身草綠和尖牙的蜥蜴傾巢而出,朝他跳去。眼看就要掩住他的視線、手腳和軀幹了,他倒抽一口氣,擠出悲戚的聲音—
「小鄧,你喝多了,到這兒就好,進去睡罷!別多想了,我扶你進去。」他推開老方,他還有沒問到的事。但不容他再多問,高粱的純度低抑了血液中的波動,身體遂展開無窮下墜,才一碰到床,他就下墜一層,再落墜,再碰底。
重獲記憶,是隔日的中午。
不知為什麼夏的節氣已然走完,鄧文成起身,坐回自己在家中固定的老位置,鼻腔依舊嗅出桂花的香氣。